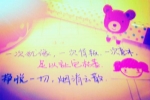阳光400字散文作文【一】
顾往昔,庐山一游,遥生得这般念好,滋生得这般朗貌,尤生得这般俊美。
八十年代,我们一行慕名苏鲁交界处的庐山,协同学友前去一游。
晨起,顶雾近山脚。举目望上,庐山貌美,翠色生荡,绿波生烟。顺着小路前行,荫荫茂密,一径蜿蜒。但见小径旁,左有杨柳相拥,右有榆槐夹道。左簇右拥,茂密叠荡。继续上行,幽幽趋坡,亦行亦趋。几多松林映遮面。或高或低,错落有致。一览清秀,苍翠生得浓浓绿烟。或波涛,或起伏,交相辉映,生生醉焉。
请上眼,那如针的松叶铺展落地皆是,偶有松塔可供捡拾留念。突地一声尖叫“啊呀”。闻得一女生惊叫,抬望眼,交错的松枝上,擦身居有松鼠成溜烟窜去。且不知,是我们一行惊扰了这松鼠,还是松鼠侵扰了我们一行。
但见得松鼠居枝翘首,举目相望,似乎有讶惊。望着我们这些陌生的不速来客,又似乎在相探。进得山,也许这巧小的松鼠便是这大山的杰灵。见那巧灵的松鼠,毛色俊秀,隐隐生光,顺滑生色。行动悠远,尾巴高高地卷翘着,一双黝黑的眼睛晶亮生光芒,尤显灵性非常。
到了半山腰上,乍细看,松树上竟有爬动的虫蛹,方言人称“松虎”。这时候也不知道是谁说了一句,“松虎能吃的”,这下提醒了我们几个。于是摘采些许,生火烤食。原来,真是挺香的,确确的野味。大山里的,就是不一样的。那番滋味,那番味嚼,至今口留余香,回味依然。据说这东西不能食用得太多,否则,食用者嗓子会起毛生烟的。
有道是“剩十里半九成”。近得山顶,方觉路陡坡峭,崎岖无比。感觉中愈上愈难,越来越艰。高险处,有一种不敢俯视于山下。回顾身旁,尤在云里雾里,不曾料,山下风静,山上风急,呼呼的山风从自己的身边掠过,吹拂过来的云雾,渐渐慢散开去,如云泊,如烟荡,给人一种荡胸生层云的愉悦!
雾,慢散在脸上,抚在身上。亦潮亦润。纵人人确是很累,终是掩饰不住清心,掩饰不住那种赏心悦目,那种沁人心脾的愉悦。几多轻松,几多欢悦,几多惬意!一朵浮云走来,伸手可及,一慢雾散去,触手可及。似梦如幻,直教人恨相见晚!
举目远眺,远望山下,不可不谓“一览众山小”。这庐山南北,兀的是山连山,山套山,山中有山,山外抱山。南北横亘数百里,不失为海岸线之后的陆路国防线。看那山山起伏,交相辉映,山山迥异,各不雷同。感觉着叠状的群山,感悟这跌宕的山峰。这绿色的翠,纵是让来者赏心悦目,终是添醉,添痴,添恋念。卷舒中,心生醉焉,眷恋中一览目阅。
昨夜,我做了一个梦,似是游览这仙境庐山!
阳光400字散文作文【二】
??中散文:冬日里的阳光这个冬天,异常寒冷;这个冬天,没有大喜大悲;这个冬天,没有雪中送炭的温暖;这个冬天,没有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举;这个冬天,有的只是努力从冷漠中挤出的一丝金光。
又是新的一天开始了,霓虹灯在一瞬间都失去了光彩,取而代之的是各种鲜亮的衣裳和锃明发亮的皮鞋,他们与高大的`写字楼融合,与这个繁华的城市相衬映。即使现在是寒冬,即使道路两旁的积雪还未融化,但这些衣裳、皮鞋们从未放慢过自己的脚步。呼!这个冬天,似乎比以往都要冷啊!
或许根本不会有人注意到,角落里,还有上帝为他们施舍来的一点温暖。
一个老乞丐,跪在一个垃圾箱旁边,双手合十,不停地磕着头,面前放着一个豁口的茶缸,他仿佛在祈求着人们的关注与施舍。可这一切的景象都与这个城市太不附了,不符到甚至没有能得到人们的关注。就在这时,一个小男孩跑了过来,双手托着五个硬币给他,眼睛不停地眨着,他在等待乞丐的接受。乞丐忙要去接,可就在这时,男孩又把手收了回来,并用思考的眼神打量着他。老乞丐想要去抢,那可是他几天的饭钱啊!可是他不敢,因为孩子的爸爸正站在旁边。小男孩忽然将手放到嘴边,使劲地吹了几口气,然后两手合着又将钱递给乞丐:“爷爷,这样的钱就不会冻着你了,你还能取暖呢!”老乞丐的眼刹那间湿润了,他颤颤巍巍地接过了钱,目送着跑远的男孩,又将钱暖在了心口。这些钱,虽然面值不大,但它带来的温暖远远超过ATM取款机中的红钞。这些硬币,在这个冬天,升华成男孩的笑容,老乞丐浑浊的眼泪,和这个寒冬的无限大爱。
在这个城市中,其实处处弥漫着点点温暖,它被这些高跟鞋和皮鞋们踢来踢去。每天,都有城市中的人向写字楼中倾倒“不公平””愤怒”的黑水,这些黑水,渐渐吞噬了这些微弱的光。这个城市的末日,就是这些写字楼吐出黑水淹没星辰的日子。
这个冬日的阳光,外的光芒,内的温暖。
阳光400字散文作文【三】
??学生叙事性散文:阳光下的藤椅“吱咯,吱咯”,一阵熟悉的响声飘入耳鼓,我知道姥爷一定又躺在藤椅上欣赏那些花了。
八十出头的姥爷,身材枯瘦枯瘦的,腰板却还挺得直。头发已经花白了,山中老藤似的皱纹爬满了脸颊,姥爷常常感叹,“岁月不留人哪!”
我一直有点畏惧姥爷。记得很小的时候,我弄折了他的花,姥爷大发雷霆,竟然当着爸爸的面,拿扫帚打了我一顿。后来,姥爷提起这事儿,那时,他也是坐在藤椅上,眯着双眼,轻轻说道:“这些花可都是有感情的,它们陪我好多年了。现在我没事的时候,给它们浇点水,翻翻土,看它们有没有开花,我的心情就很好了。”姥爷似乎在自言自语,可他平静的口吻和阳光下安详的面容,着实让我愧疚了好一阵呢!
姥爷不是很爱说话,闲暇的时候,除了摆弄那些花,就是戴上那副老花镜,翻翻破旧的辞海。小时候,我有不知道的词呀、典故呀、人物呀,只要跟姥爷说一声,他就会戴上他的老花眼睛,翻开厚重的辞海,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那时,在我的眼里,姥爷仿佛就是一本厚厚的辞海,无所不知。
当然,尤其让我对姥爷心生敬畏的是姥爷的一身正气。姥爷以前是财务科的科长,这是多么令人眼红的位置啊,可是姥爷一直两袖清风,只管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他的傻,成为同事私下的笑料,连姥姥、小姨们也怨姥爷老实。可姥爷很坦然,“为人不做亏心事,不怕夜半鬼叫门。什么叫心底无私天地宽啦!就我这样的'。”姥爷说完,还重重地拍拍胸脯。
我一天天地长大,姥爷却在一天天地老去。可我对姥爷那种畏惧依然存在。我想,这不是别的,正是被他内在的威严所折服,正气所感染的缘故吧!然而不管怎样,他终究是那个坐在藤椅上的慈祥老人,是疼爱我的姥爷。
午后的阳光温柔地洒在藤椅上,那些花儿在空气中摇曳,我看到姥爷脸上浮着满足的笑意。这个画面在我的记忆中定格。
阳光400字散文作文【四】
黑夜下的街道显得更冷清了许多。
我如此喜欢着这个远离城市,只有平砖碎瓦的小地方。
就像一种隐居。
就像,某种疏离。
下班之后,挤过人肉饼后的公交,穿过城市繁华明明灭灭的光影。沉默中淡然且淡漠地以一种上帝的姿态注视着这短短旅途中形形色色的人群。
这让我想起小时候一个人穿越村外那个荒芜的坟场。多像啊,一样让人感到烦闷,一样让人感觉到窒息的绝望。
有许多骷髅在眼前摇晃,他们在笑,他们在闹,他们在低声交谈,偶尔向我投来一两瞥混不经意的目光。似十月凌晨里起床第一卷寒风。他们说着我听得懂听不懂的语言,在他们的大世界里游离张狂。
下车,深吸一口郊区里流畅到带清香的空气。便不再想走。
哦,忘了说,我住远离人群的风景区中,“十里河滩,湿地公园”。早上有金灿灿的阳光从尖头山侧升起,有蕴育朦胧轻纱似的薄雾笼罩的河床,以及那些水鸟、白鹭、话梅还有百灵。我总能在等公交的间歇间从那里寻到我梦的痕迹。
盯着久了,也就好似自己走在这样一场梦里,身前身后都是薄薄的一层我怎么看也看不透的雾,眼神无法聚集在远方,只能微微向前张开手,向前慢慢走,摸索着穿过林,穿过一个个串联起来的故事。
做完梦,亦或者梦还未完,公交车就像个姑娘似的来了。公交车本来是好的,记得初中时看过一句话:“希望总在未班车中开来”喜欢了很多年。可是现在,事实告诉我,我所喜欢的,往往将我载入我所讨厌的厌恶的,极度排斥的环境中去。 而我,却无力去反抗。
命运总是在妥协中四平八稳向前行着。每一个生命,或者类似于我这样的生命,都像是一个个早已在工厂流水线上排好了队向前行的产品。
尔后等待命运的大手将你归划到次品,还是合格品的行列。
那些顺从者的合格品,便端着红酒杯,出入酒绿灯红的世界;而次品,则在街角与秋风,与尘埃,进行一场思想上的交流。
但,人们只需合格品,因为他们站着高,享受欲理上的快感。
次品,在精神的田野上开垦,就算硕果累累,也终只在树的尸身上闪光。
其实,晚上的那条河那坐山,那些精致到让我沉醉的风景,我是看不到的。
也许,正是这样一种不可见,让我能常常走进它的梦里,走近它。听它的心跳,到它的温柔。
正是这样一种不可见的可见,让人充满向往,在绝望里为生命的生,所挂住的最后一丝留恋。
爬上五楼,打开房间前窗的纱窗,推开后窗的门,甩开鞋子打着赤脚然后泡上一杯热茶,或仰身倒于床上闭眼睡觉或举起一本在前晚还未看完的书或者拿出本,继续昨夜凌晨里的纠结。
多数时候,我是直接闭眼睡觉的,累或者其他。我不知道,要我说,也说不出来。
然后,到晚十来点的时候,起床,下楼,一遍一遍穿堂而过这片小建筑群里的街巷。穿越每一盏灯,抚摸每一块石,转角跑到一个陌生的角落,然后落寞地笑,间或抽上一根烟。
烟,慵懒地在夜里慢慢向上升,慢慢变淡融入黑的色里,好比一场朝圣,一段灵魂在解脱里向着天堂而去。
好像,一段故事。终被时间的庞大暗黑给吞噬。
“想起一个离开的人,就像拿起一把无形的刀”,某次,我对朋友说。他告诉我,所有的揪心,只是因为有一只手在紧紧握住回忆,握住一段枯萎了,再也复回不了的情。 我就笑,然后告诉他们滚。然后,他们就真的渐渐全部不见了。
这样也好,就没人再来打扰我,就没人再来说些不中听的话,做些连他们自己都明白的无任何意义的事了。
我也乐得清静,不是都说岁月静好岁月静好吗?这样真的挺不错的。
至少,我乐得做自己,不必管对错。
至少,我知道,在那遥远遥远的地方,存在着这样一个地方。
让死而复生,让时光回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