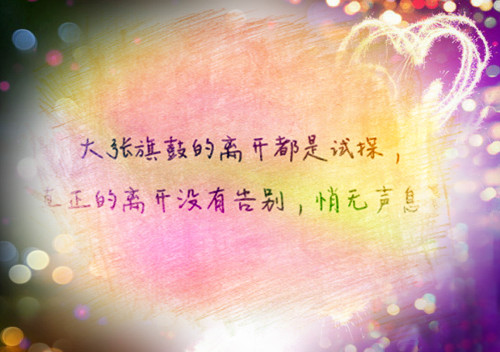
和姥姥那一段温暖的时光作文【一】
初一也结束了,总觉得很怀念,好像昨天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小学,步入初中时代,五年看似漫长,到了最后才会觉得时光飞逝仅在挥手间。
稚气没了,换来的`是成熟;天真没了,换来的是沉稳。
蓦然回首,看见了曾经的自己。微微泛黄的旧照片上,还有当年的模样。一头乌黑的长发,忽然有些落寞。那个扎着马尾,笑起来就眯着眼像弯弯月牙儿的女孩不见了。
的确有很大的变化,我常常想,头发剪了,利索些。眼睛已不似那般纯净清澈,是懂得多了,也夹杂着一丝丝浑浊。
那年是一年级。踏入校门,什么也不懂。抬头望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懵然地戴上红领巾,举着手,跟着台上的姐姐宣誓。
那年是二年级。秋风又起,度过了学校的第一个暑假,踩着一地柔软的落叶,重新走进了这个校园,重新认识了这个校园。
那年是三年级。班里人都熟络起来,课间一起玩耍,一起打闹,笑声像晶莹剔透的琥珀,碎落在地上,与暖阳交合,散着金光。
那年是四年级。冬天操场上白茫茫一片,总会有几个长大的身影在那。他们在堆雪人,脸红扑扑的,手也冻僵了,却依然捧起一团团雪,掷下雪白的希望。
那年是五年级。毕业的讯息在脑中传递,像钟声,敲击着心灵。同学录上留下不同的笔迹,但都是满满的祝福。
现在,一个星期仅能回首两眼的建筑,在我心里,容颜已改。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
童年,已是闭上眼睛再也梦不到的神秘。
只能回忆。那笑声,那身影,那岁月,那一段美好的时光!
和姥姥那一段温暖的时光作文【二】
那是在一个晚上,当我们刚刚准备吃饭的时候,停电了,我们只好拿了两根蜡烛照亮来吃饭。吃着吃着,爸爸看着蜡烛突然对我说:“今天晚上停电,没什么事可做,我们就来试试将手指划过蜡烛上的火焰吧!”我听了,心想:我这么胆小,怎么可能敢。而且火可是有几百度的温度,这样一碰,手不就烧坏了?于是,我对爸爸说:“你先来试试,不然我可不敢。”说完,爸爸马上用手指在火焰中滑动。我看得眼都花了,十分佩服爸爸。爸爸表演完就对我说:“我手滑的是火焰的焰心,温度只有几十度,根本就对手指一点伤害都没有,只是有点暖和。”我听了半信半疑,便问:“我不信,火的温度本来就很高,哪里有分什么焰心、外焰和内焰。”爸爸于是笑着说:“这就是你科学没学的原因,这是科学道理。”我听了,就说:“我们现在还没教到这些,所以我不知道。”爸爸说:“我试过了,现在该你试了。”我听了,就说:“试就试,谁怕谁?”我说的理直气壮,可心里不知道有多害怕,但为了证明我不胆小,我就只能去试试了。我慢慢地将手从口袋里拿出,伸出一只手指头,十分舍不得往那边伸过去,好像是在告别一样,永远也见不到了。我对准了目标,一咬牙,就马上划过了蜡烛。我马上看看我的`手指头,完好无损。我的沉重的心终于落了地。我相信了爸爸说的是对的,顿时充满了信心,用手指在火焰中来回穿梭,行动自如。爸爸看了也为我感到高兴,说:“没想到你竟然做到了,我以为你不敢呢!”我说:“还不是因为你告诉了我道理,也给我示范了一遍,不然我怎么敢啊!”
那一段时光虽然渐行渐远,但真是让人难忘啊!
和姥姥那一段温暖的时光作文【三】
老人穿一件普通的衬衣,胸上几枚军功章却是赫然醒目。他脚步稳健,脸上半是激动,半是兴奋。他坐在那儿,背挺得笔直,一副军人的模样与气势。
我们相对坐下,一行中的一位少先队员,捧上了红领巾,告诉老人“我们要将这红领巾献给您,为您系上它,这代表红旗的一角。”
老人是惊喜,是激动,似还有些许的紧张。他挺着腰坐在那儿。少先队员缓缓上前,为老人系上它。那一抹鲜红的色彩在老人的胸前漾着,老人的脸上满是欣喜。
我们慢慢谈着,老人絮絮叨叨地讲着他的。点点滴滴的小事在老人的口中缓缓流淌出来,那些岁月在老人的每一根皱纹间流露,流入我们的心田。
那段历史离我们如此之遥远。老人娓娓讲来,将那段活生生的历史拉到我们面前。从飞机轰炸,讲至美军的军舰巡逻;从天气严寒,讲至食物贫乏。那是一些平凡而又震人心魄的故事。
讲至激动处,老人便轻轻晃动着身子,那根红领巾,跟着,轻轻晃动,如此耀眼。
抗美援朝,抗日战争,只在那些印满铅字的书页上呈现,黄继光,邱少云,那是多么神化的人物。这些统统显得可望而不可及,遥远而空洞。
而一位老人,却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时,让我们看到了那段往事。那是活的',活的照片,活的子弹壳,活的军功章,活的复员证。在今天,远离战争的和平年代,不知触摸这些算不算得上是一种奢侈。
凉风吹来,红领巾在老人挺起的胸脯上晃荡。随着那抹红色,这已不止是了解,我们已走进了那段历史。
老人的腰板是笔直的,他的胸脯顶起了那根鲜艳的红领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