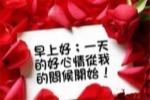民间艺术高中作文【一】
为了争占母鸡,两只公鸡打了起来,其中一只把另一只打跑了。那只被打败的只好躲进有遮盖的地方,那只打胜的却飞到高墙上大喊大叫。这时一只鹰猛飞过来,将他抓了去。这以后,那只被打败的公鸡平平安安地占有了那些母鸡。
民间艺术高中作文【二】
惊蛰象征二月份的开始,会平地一声雷,唤醒所有冬眠中的蛇虫鼠蚁,家中的爬 惊蛰民间习俗“打小人”
虫走蚁又会应声而起,四处觅食。所以古时惊蛰当日,人们会手持清香、艾草,熏家中四角,以香味驱赶蛇、虫、蚊、鼠和霉味,久而久之,渐渐演变成不顺心者拍打对头人和驱赶霉运的习惯,亦即“打小人”的前身。
所以每年惊蛰那天便会出现一个有趣的场景:妇人一边用木拖鞋拍打纸公仔,一边口中念念有词地念:“打你个小人头,打到你有气冇定抖,打到你食亲野都呕”的打小人咒语。
民间艺术高中作文【三】
中国的民间传说白虎是口舌、是非之神,每年都会在这天出来觅食,开口噬人,犯之则在这年之内,常遭邪恶小人对你兴波作浪,阻挠你的前程发展,引致百般不顺。大家为了自保,便在惊蛰那天祭白虎。所谓祭白虎,是指拜祭用纸绘制的白老虎,纸老虎一般为黄色黑斑纹,口角画有一对獠牙。拜祭时,需以肥猪血喂之,使其吃饱后不再出口伤人,继而以生猪肉抹在纸老虎的嘴上,使之充满油水,不能张口说人是非。
民间艺术高中作文【四】
一天,森林之王狮子郑重地宣布:“下个星期一我要在森林上空举行飞鸟比赛,看哪只鸟先绕着森林飞完一圈。请鸟儿参加比赛。”
小鸟们一听,是绕完森林一圈,所有鸟儿都向后退了一步,只有三只鸟儿站了出来,其中,两只是燕子,一只叫快快,另一只叫奔奔,站出来的第三只是一只乌鸦,叫慢慢,它的毛灰灰的,嘴巴大大的,长得可难看了。
乌鸦得金牌快快和奔奔都在偷偷讥笑慢慢。慢慢早就发现了,可是它就当没有看见一样。
慢慢一回家就锻炼。早上和晚上它都要出来跑步,中午做仰卧起坐……可是那两只骄傲的燕子,懒洋洋地躺在床上睡大觉,什么也不干。
星期一到了,大家都准时到了现场,那两只燕子才慢吞吞地飞过来。
比赛开始了,那两只燕子遥遥领先,乌鸦还是落后了。但是,乌鸦坚持下去了。那两只燕子回头一看,乌鸦还在后头呢!它们就玩了起来,玩着玩着,它们就停在一颗树上休息,没想到它们睡着了。
等它们醒来,乌鸦早绕完森林一圈了。
狮子拿起金牌,递给乌鸦。乌鸦小心翼翼地接过金牌。那两只燕子眼巴巴地看着乌鸦兴高采烈地拿走金牌。
民间艺术高中作文【五】
狗叼着肉渡过一条河。他看见水中自己的倒影,还以为是另一条狗叼着一块更大的肉。想到这里,他决定要去抢那块更大的肉。于是,他扑到水中抢那块更大的。结果,他两块肉都没得到,水中那块本来就不存在,原有那块又被河水冲走了。
民间艺术高中作文【六】
对金先生这番话,笔者起初不大以为然,甚至有些愤愤然——世界上没有跟钱有仇的人,谁不爱钱?谁离开钱能活命?如果说老外艺术家不爱钱,那些天价艺术品,那些五花八门的画商、画廊、经纪人、拍卖公司……是谁发明的?如果画家都不要钱不卖画,那些画廊、拍卖公司岂不早就关门了?那些画商、经纪人岂不早就饿死了?再说了,外国即便有不爱钱的画家,也是因为他们不缺钱,别墅住着,汽车开着……中国画家爱钱,是因为我们穷怕了,穷够了。穷则思变,穷则思富,人之常情,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但是,当冷静下来再仔细咂摸金先生的“逆耳之言”时,笔者的愤怒渐渐消退了——人家批评的没错啊!罗列的现象也完全是我们美术界的事实。再细想想,其实金先生还没说全,当代某些中国书画家早已经拥有了票子、房子、车子,但仍然“疯狂地追逐金钱”,甚至不惜“流水作业”“批量生产”,丢人啊!
毋庸讳言,我们的确是穷人乍富,好不容易有了发财的机会,心态失衡可以理解,爱钱也没有错,但是要成为真正的艺术家,成为大师,确实就不应按普通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仅仅把攫取金钱、获得物质享受作为“最高理想”和“终极目标”。因为一个艺术家如果没有崇高的理想、高尚的追求,思想境界庸俗,人格低下,其作品必定很难达到陶冶心灵、美化生活、匡正世风、流传后世的高度和水平;而一个国家的艺术界,如果整体沉溺在追逐金钱、满足物欲、铜臭弥漫的状况里,就确实是严重的病态了,如不痛下决心根治,最终必然要遭到国际社会以及子孙后代的鄙夷、嘲笑、批判和唾弃。
一方面,艺术家也是肉身凡胎,不可能完全抵御金钱物质的诱惑;另一方面,纯粹的艺术创作又天然排斥“唯利是图”“金钱挂帅”。那么,艺术家究竟应该如何正确、妥善地处理艺术与金钱的关系呢?
笔者认为,无论在何种背景、何种条件下,要求艺术家人人做到“重义轻利”或“重艺轻利”都是不现实的,但是如果在艺术界遵循“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原则,提倡“重利重义”“重利重艺”,号召艺术家“爱钱不忘爱艺术”“爱钱更要爱艺术”,应该是既符合人性又切实可行的措施。
“重利重义”“重利重艺”,即是对待金钱与艺术二者并重,互不矛盾,互不排斥。具体到书画家个人,可以聪明,但不可以精明;可以经商,但不可以做商人。书画家与购藏者是特殊的买卖关系,出售的作品一定要物有所值,性价比合理,即让顾客花钱买到好东西。在这方面,许多中国古代艺术家做出了正面榜样,清代著名书画家郑板桥就是一个突出的.范例——他痴迷艺术,甚至弃官从艺,作书作画精益求精,水平登峰造极,但他也绝不讳言自己爱钱。在那篇著名的《润格》中,郑板桥不仅开列出真金白银的书画价码,还特别强调“要现钱”。实践证明,顾客掏钱买了郑板桥的书画,无论在当时,还是留传给子孙后代,没有一个人是吃亏上当的。
郑板桥重利,但更重义。在“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时候,郑板桥毅然选择“舍利取义”——他曾郑重宣布自己的画是“用以慰天下之劳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人也”“农夫乃为天地间第一等人”。普通劳动阶层的朋友虽然少钱或没钱,但如果真心喜欢他的字画,他不仅绝不再坚持“大幅×两、小幅×两”,还经常无偿赠送。
当代画家吴冠中先生是爱艺术胜过爱金钱的典型——他在物质享受面前表现出超乎寻常的清高和淡泊,尽管作品价值连城,名声如日中天,却甘愿终生布衣蔬食,居旧屋陋室,废寝忘食、呕心沥血地画画、写文章,绝对堪称金兑庭先生所说的“对艺术无比虔诚敬畏”“一心一意在做自己内心里的事情”的“纯粹”艺术家。
但愿我们中国艺术界里少一些“疯狂地丢了魂一样地追逐金钱、房子、名车”的人,多一些郑板桥、吴冠中这样“爱钱更爱艺术”或“爱艺术胜过爱金钱”的艺术家。
民间艺术高中作文【七】
一般而论,我们在实物中感到兴趣而要求艺术家摘录和表现的,无非是实物内部外部的逻辑,换句话说,是事物的结构,组织与配合。艺术家改变各个部分的关系,一定是像同一方向改变,而且是有意改变的,目的在于使对象的某一个“主要特征”,也就是艺术家对那个对象所抱的主要观念,显得特别清楚。这特征便是哲学家所说的事物的“本质”,所以他们说艺术的目的是表现事物的本质。
艺术家必须是生性孤独、好沉思、爱正义的人,是个慷慨豪放、容易激动的人,流落在萎靡与腐化的群众之间,周围尽是欺诈与压迫,专制与不义,自由与乡土都受到摧残,连自己的生命也受到威胁,觉得活着不过是苟延残喘,既不甘屈服,只有整个儿逃避在艺术中间。
文明过度的特点是观念越来越强,形象越来越弱。日常的精神活动从此变为纯粹的推理。所谓精神状态是指一个人的观念的种类、数量、性质。但人身上还有比观念更重要的东西,就是他的结构,也就是他的性格,换句话说是他天生的本能,基本的嗜好,感觉的幅度,精力的强弱,总之是他内部动力的大小和方向。
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一章,丹纳谈到了很多当时意大利仇***、下毒、暗***的资料,这对了解《罗密欧与朱丽叶》故事的背景很有帮助。(十五世纪的意大利)理论家中最深刻的一个是马基雅维里,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还是正派的爱国的人,有很高的天才,写了一部书叫做《论霸主》,说明奸诈和凶恶是正当的,至少是许可的。说得更正确些,他既没有许可,也没有辩护,他无所谓义愤,把良心问题搁在一边:他只用学者和洞达人情世故的专家身份来分析,解释;他提供材料,加上按语;古代生活的所有这些特点,都出于一个原因:就是非常平衡而简单的心灵。没有一组才能与倾向是损害了另一些才能与倾向而发展的,心灵没有居于主要地位,不曾因为发挥了任何特殊的作用而变质。少受过度文明的奴役,因此他更接近于本色的人。
所有这些对立地情形,归结起来只是一种全新地不假思索地文化和一种煞费经营而混乱的文化的对立。希腊人方法少,工具少,制造工业的器械少,社会的机构少,学来的字眼少,输入的观念少。遗产和行李比较单薄,更易掌握;发育是一条直线的,一个系统的,精神上没有***乱,没有不调和的成份,因此机能的活动更自由,人生观更健全,心灵与理智受到的折磨、疲劳,改头换面的变化,都比较少:这是他们生活的主要特点,也就反映在他们的艺术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