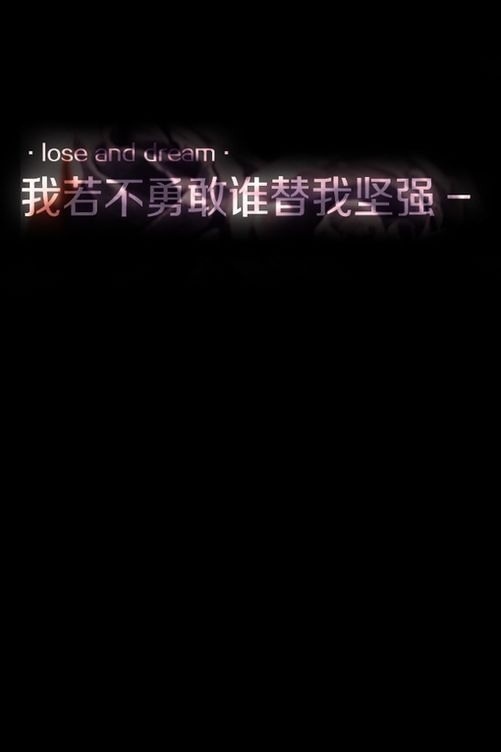
熊猫英语作文几句话【一】
在外滩看见一个警察打人,没有缘故,只是一时兴起,挨打的是个十五六岁的穿得相当干净的孩子,棉袄棉裤,腰间系带。警察用的鞭,没看仔细,好像就是警棍头上的绳圈。“呜!”抽下去,一下又一下,把孩子逼在墙根。孩子很可以跑而不跑,仰头望着他,皱着脸,眯着眼,就像乡下人在田野的太阳里睁不开眼睛的样子,仿佛还带着点笑。事情来得太突兀了,缺乏舞台的人往往来不及调整面部表情。
我向来很少有正义感。我不愿意看见什么,就有本事看不见。然而这一回,我忍不住屡屡回过头去望,气塞胸膛,打一下,就觉得我的心收缩一下。打完之后,警察朝这边踱了过来,我恶狠狠盯住他看,恨不得眼睛里飞出小刀子,很希望我能够表达出充分的鄙夷与愤怒,对于一个麻风病患者的憎怖。然而他只觉得有人在注意他,得意洋洋紧了一紧腰间的皮带。他是个长脸大嘴的北方人,生得不难看。
他走到公众厕所的门前,顺手揪过一个穿长袍而带寒酸相的,并不立即动手打,只定睛看他,一手按着棍子。那人于张惶气恼之中还想讲笑话,问道:“阿sir是为仔要我登牢子?
大约因为我的思想没受过训练之故,这时候我并不想起阶级革命,一气之下,只想去做官,或是做主席夫人,可以走上前给那警察两个耳刮子。
在民初李涵秋的小说里,这时候就应当跳出一个仗义的西洋传教师,或是保安局长的姨太太(女主角的手帕交,男主角的旧情人。偶尔天真一下还不要紧,那样有系统地天真下去,到底不大好。
熊猫英语作文几句话【二】
成长的道路是艰难的,而我正在成长的道路上,以坚韧顽强的性格行走着。有压力但没有屈服,有疼痛却没有溃败。我就像一只破茧而出的碟,经历着成长的喜悦与阵痛。
在去年寒假,正处于叛逆期的我总是处处和父母作对。父母说什么不听什么,弄的父母很头疼。而我还总是以为:我长大了,成熟了,有了自己的思维了,能自己做主了,你们不用管我了!但在这个寒冷的冬天,表姑却给我上了一课……
“不!我就不!我又声嘶力竭地和妈妈嚷起来。其实妈妈就是让我烧一壶水,力所能及的事情为什么不做呢?而我却口是心非地说出了“不”。在一旁的表姑见我这样,不慌不忙地走过来说:“天存,我能和你聊聊吗?我在隔壁的屋等你。”表姑是个鬼点子特别多的人,我这次倒是要看看表姑葫芦里买的是什么药!
我敲了敲门,走了进去。表姑已经在那里了,她让我坐下,没等我问,她就先发话了:“天存,你先在正处与青春期,叛逆心理是常有的。度过青春的河,穿越黑暗的隧道,都是每个人必经的道路。而这个道路却是十分艰难的。”“艰难?成长会有什么艰难?”我不解地问道。表姑耐心地回答我的问题:“这种‘艰难’更多来自于内心的惶惑与焦虑。诸如:升学压力、人际关系。在青春期的你们看起来就像荡着情绪的秋千。而家长就是疏导你们内心风暴,陪伴你们健康成长的良师。所以,现在在青春期的你,应该更好的回报父母,而不是和父母作对,要知道,化蛹为蝶,成长终究是要承担的。”
表姑的一番话,使我又震撼又感动。是的,成长是需要承担的,就像石块下的草籽儿,终究要在重压之下顽强而又愉快地释放生命的能量,发芽,出土,挺立,迎着风雨沐浴着阳光。
熊猫英语作文几句话【三】
有个朋友问我:“无产阶级的故事你会写么?”我想了一想,说:“不会。要么只有阿妈她们的'事,我稍微知道一点。”后来从别处打听到,原来阿妈不能算无产阶级。幸而我并没有改变作风的计划,否则要大为失望了。
文人讨论今后的写作路径,在我看来是不能想象的自由——仿佛有充分的选择的余地似的。当然,文苑是广大的,游客买了票进去,在九曲桥上拍了照,再一窝蜂去参观动物园,说走就走,的确可羡慕。但是我认为文人该是园里的一棵树,天生在那里的,根深蒂固,越往上长,眼界越宽,看得更远,要往别处发展,也未尝不可以,风吹了种子,播送到远方,另生出一棵树,可是那到底是很艰难的事。
初学写文章,我自以为历史小说也会写,普洛文学,新感觉派,以至于较通俗的“家庭伦理”,社会武侠,言情艳情,海阔天空,要怎样就怎样。越到后来越觉得拘束。譬如说现在我得到了两篇小说的材料,不但有了故事与人物的轮廓,连对白都齐备,可是背景在内地,所以我暂时不能写。到那里去一趟也没有用,那样的匆匆一瞥等于新闻记者的访问。最初印象也许是最强烈的一种。可是,外国人观光燕子窝,印象纵然深,我们也不能从这角度去描写燕子窝顾客的心理吧?
走马看花固然无用,即使去住两三个月,放眼搜集地方色彩,也无用,因为生活空气的浸润感染,往往是在有意无意中的,不能先有个存心。文人只须老老实实生活着,然后,如果他是个文人,他自然会把他想到的一切写出来。他写所能够写的,无所谓应当。
为什么常常要感到改变写作方向的需要呢?因为作者的手法常犯雷同的毛病,因此嫌重复。以不同的手法处理同样的题材既然办不到,只能以同样的手法适用于不同的题材上——然而这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经验上不可避免的限制。有几个人能够像高尔基像石挥那样到处流浪,哪一行都混过?其实这一切的顾虑都是多余的吧?只要题材不太专门性,像恋爱结婚,生老病死,这一类颇为普遍的现象,都可以从无数各各不同的观点来写,一辈子也写不完。如果有一天说这样的题材已经没的可写了,那想必是作者本人没的可写了。即使找到了崭新的题材,照样的也能够写出滥调来。
熊猫英语作文几句话【四】
语言像是救赎。——题记
语言的力量强大到人类无法企及的地步。鲁迅,用语言与文字救了中国无数青年人的思想;李白,用诗句与文字救了大唐的诗坛;王羲之,用书法救了文坛字体。
语言鲁迅
鲁迅啊!你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潇潇洒洒;是“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一战成名;是“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英勇护国。你用语言与文字的魅力救中华儿女于水火,你是人民的英雄,更是语言表达的先驱!那句话的力量,使我自豪!
诗句李白
李白啊!你是“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乐观开朗;你是“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的文中武将;你是“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的百月朱砂。你用诗句与文字的魅力救大唐诗坛于危旦,你是大唐的“诗仙”,亦是人们心中的太白,更是诗词创作的高峰!那句话的力量,使我乐观!
书法王羲之
王羲之啊!你是那腐杇路上文体创作的光明,你的《兰亭集序》千古流传,生生不息。就好比那历史长河中杜甫恒古不变的爱国精神,革命流云中***坚持不懈的复兴中华,黑暗变革中列夫托尔斯泰初心永存的静等黎明。你融合了大家的文体,独创行书——天下第一行书。你用书法的特点救了文坛字体于当时。那句话的力量,使我震撼!
古往今来,多少人的多少话传达出了多少感情,都永远地停留在了的`历史的长河中。
那句话更像是救赎。——后记
熊猫英语作文几句话【五】
我永远忘不了这向话!
看着窗外三年都未开过的茉莉花,我陷入了茫远的沉思中......三年前,茉莉花飘着一地的香,散落着枝头零星的白,它飞舞着,是真正的舞,每一片都拥有着风姿。有个女孩站在那儿独自欣赏着,那种认真的眼神似乎要把花看透;我不曾想也有一个女孩和我一样爱着花。很自然,我们两个女孩走在了一起,我们都有着易安居士的多愁善感,迷恋着美,喜欢用笔尖磨写磨砺人生,我相信我们有着最真的友谊。
可是一切都来得太快,令人猝不及防。那天余晖洒在脸上很凄很凄。我拿着送给她却已被画得一塌糊涂的照片,我是个敏感的人,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们绝友吧!”我破口而出。后来我不知道她是如何含着泪离开,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哭得一塌糊涂,只知道那是花落的季节。
后来,我知道这是个误会,是她不小心遗失了,被他人刻意画的,我后悔,后悔说过这句话。
有一个网,丝丝缕缕纠结着内心最深处撕心裂肺的'痛。每当我看到茉莉花被风刮得遍体鳞伤,就犹如一个个突出的棱角刺得心鲜血淋淋。难道连花儿也想抬起我们这短促的回忆,想收起当天我说过的这句话?茉莉花曾悠悠地快乐过,而如今却只有寂寂地凋落去,如果我再见到你,我一定会对你说:“我并不想绝交。”
有些花,谢了就不再开;有些话,说了就不能收回,逝去的友谊,消逝在似水流年里,淡漠了几许情感,几多岁月……
熊猫英语作文几句话【六】
我原本对自己的人生怀满信心,可是,一次考试把我打垮了,从此我对人生根本没有希望。
这时,张老师的一句话,改变了我对人生的看法。有一天,我们正在上《种一片太阳花》,张老师说“课文里的太阳花很坚强。作为一个人,要是不坚强,就容易被打倒,所以那些学习不好的学生只要认真,坚强起来,也一样可以变成天才。”听了这话,我改变了对人生的看法。是呀,只要坚强起来,就一定会成功。人生不过是一场游戏,是一场有意义的游戏,只有坚强才有自己的归宿。从此以后,我就坚强了起来,向着目标进发。现在,我已经成了我们班的“东方不败”。
还有一次,我本来是一个不喜欢看书的'人,家里人都说我只会看电视,可是老师说:“读书吧,多得知识,绝对不是坏事。”由此,我想起高尔基说的:“热爱书吧,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后来,我就立下了一个志向,就是考上清华、北大,来报答老师和父母的恩情。
我总忘不了那几句话,这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几句话,因为它改变了我的人生,让我健康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