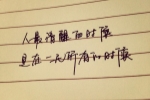推荐中国古典文学的英语作文【一】
下卷的文学史,可以看出一条循着动荡不安、向现代化演进的路线,时间交汇到现代,波澜壮阔的文学长河尽现眼底,只是它在不停地流动着,看得人目眩神迷,极力望向长河的源头,那源头隐隐约约的,似真似幻。
我就像一个在河边玩耍的稚子,不经意地看了长河一眼,大概窥得它的形态,又继续玩耍起来。就像稚子会问“什么是河”一样,我掩卷思索的是“什么是文学”,顺带着还有“什么是作家”“文学的使命是什么”“作家的原则是什么”……
走在仲春的暖融里,天边飞散着稀薄的红霞,太阳要坠下去了,马路上车来攘往,人们都匆忙奔驰在回家的路上,文学,这个时候会有人想起吗?它跟现实的人生有多大关系呢?漫长的文学史中,绝大部分的时间,它好像跟平民大众没什么联系,珍贵的书籍掌握在精英阶层手中,文学创作也由有闲有钱的他们自觉承担,“黔首”“白丁”所了解到的文学边角料,已是上层人士咀嚼消化过的。
这样的现实难免让人失落,我们大部分人只是平民大众的一员而已,文学于己有没有关系可以不用太挂心,但是,为什么人心总能被杰出的文学作品打动、同声共气地沉醉流连其中呢?
细思起来,文学,只是庞杂社会里的一个分支而已,在万物、宇宙、历史环境里,它显得那样细弱,但仅仅这么想,又过于狭隘,喜怒哀愁,风俗人情,“道与理”“义与真”,种种种种,都能蕴藉其中,可以到达人性和心灵最遥远的边界。可是文学究竟是什么?载道的工具?气韵的流转?个人的表达?象征主义、印象派、抒情派、后现代、现实主义的流派分割?越是用具体的名词描述文学,越使我迷惑于它的本质,以致彷徨惊惑,狼狈而逃。
作为文学作品的创作者,作家是文学类别里的主体,可是本书中用“作家”来称呼古代的文人时,令人感到诧异,还会有时空的置换感。“作家”这个词太新,古时的文人大概没有职业作家的自觉,后世所谓的文学作品,只是文人日常生活的一小部分“余烬”而已吧。漫长的历程中,“作家们”有何特质?又有什么共同特点呢?下笔的时候,他们在想什么?有人以笔为枪,有人沉湎雕琢,有人依附于意识形态,有人声称艺术、人性与自由高于一切,还有,文人相轻、讨伐攻讦、因文获罪……文学的领域,一如其他地方,也有肮脏、肤浅、斗争,因为,文学的背后是一个个的人。
在明末清初、清末、民国、抗日战争期间,时代动荡交迭,乱象纷呈,文人、作家,有着种种不同的选择,人生的际遇与家国命运纠缠在一起,站在文学史的高度回望他们人性的挣扎,更多的是怜悯和悲怆,历史的天空江风浩荡,空余一声声惊涛回响。
原书是叙述到2000年左右的,而出于某些原因,大陆版只截取到1949年,看不到全貌,最后一章突然中断,有些遗憾。这突然的失落感惹人思绪绵绵,是的,完结了,就这么结束了,扫过后面附录的几十页人名、作品索引,如再看一眼长河微澜,涛声远去了,看似归于平静的河流还会亘古不变地流下去,过去,现在,将来,永远。
推荐中国古典文学的英语作文【二】
以前我对这套书是不以为然的,认为里面肯定很多陈旧的模式化思想。因为欧丽娟老师的几次提及,我觉得或许里面有不少可取之处。故阅读。
这套书在评价储光羲的田园诗《田家即事》时,认为前半段朴素真切,但对后半段里“拨食与田乌,日暮空筐归”的“恻隐”之心,却认为是很无聊。在后面更是指出储光羲为了子孙广田圃,是庸俗的地主意识。
起初,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忍不住发笑了。这也能评价无聊不无聊,不过就是把自己筐子里的东西全给田乌吃了呗。
但转念一想,这当真是完完全全的恻隐之心吗?恐怕未然,恐怕有一部分的是出于储光羲自己的田园之趣。他要是用白描手法写自己的这一行为,不加“恻隐”这两字为自己解释,或许不会招来非议吧。
再一想,那个年代的编写者们,条件远远不如我们现在。然后我又想起小时候,家里人是不准我剩米饭的,甚至吓唬我说要剩几颗米就要掉几根头发,长大以后就是个大秃子。是勤俭美德吗?或许是。但也有很大一部分,是物质条件真的不好。更远以前的60年代呢?恐怕编写者们是极其可惜那一大筐喂了田乌的粮食的,若是给人,那或许就少了个人挨饿的一餐。他们在心痛一千多年前的那一筐子粮食。
仍有些好笑,但却也令人心酸。他们希望的是人人有饭吃,不挨饿,不要有少数人的剥削和浪费来加剧普通人民的生活艰辛。
看到大家的打分都挺低的,我想写下这篇书评。或许没有多少价值,甚至还会觉得我在小题大做,但还是想为过去条件远不如我们的编写者们说一两句话。
这本书中也有很多真知灼见,没必要拘泥于那些令你反感的模式化的政治术语。
借用欧丽娟老师的一句话:遗忘和误解,远比尊重和了解容易得多。
推荐中国古典文学的英语作文【三】
郑振铎的这套书写于1930年代,所以整体上,有着明显的时代感,措辞、情绪,生发着“五四”后的感觉,用词新颖又古典,不经意地流露着除旧迎新的热烈,不太同于现代的书写方式。
上卷读完,极能感受到“郑氏风格”的特点,正如作者所说,有的文学史的写作是多人完成的,可能体例纷杂不统一,而一个人完成的作品会明显带有个人风格,体现个人学识态度。是的,透过他这本书,感受很深。
不知别人写文学史是否都会如此布置,但郑振铎的铺陈实在是过于全面摊开了,基本上是按人来一个个陈述,此人生平,代表词句,有名的人多说点,没什么名气的三两句带过,一个一个又一个人地这么平铺直叙着,颇有堆砌之感,看久了,会觉得累,觉得这些人都差不多,各人的代表性词句也都差不多的样子,作者怎么也不嫌累,还是在絮絮地介绍着。
但他并不是无自己喜好的,遇到喜爱的作家和文体风格,一连串的排比倾泻而下,反复比喻,言辞轻快,喜爱之情满溢而出。他是抒情的、个人化的,能感受到他对陶渊明、杜甫、新乐府、变文等作者和形式的喜爱,比如他单拎出杜甫成一个小章节,详写他的遭际和不同时期的诗,在别的作者是没有这个待遇的,比如他用了快一页的奔腾不息的各种新奇美好比喻来表现新乐府的清新自然,滔滔不绝不加修整的情感铺面而来。这些时候的他是从漫无边际的陈列里蹦跳出来歌唱着的。
对大大小小诗人、词人、文章作者和作品,历来有很多的评论集囊括点评,所以郑振铎几乎是博采古代的评论来评价一个人,左一句诗品右一句诗话,文白夹杂,细碎分裂,而不是全然地出于他自己的感想。可以看得出他很下工夫,搜集了不同朝代的人的评述相互参照,当然,有时他也会对前人的定论持不同意见,直言他自己的见解。
只是,述那么多作者的生平,他的表达方式几乎都是凝结史书记载的“官位变迁”,三两句讲完一个人都做了哪些官,卒于什么官位和地方,什么谥号,有的会摘一点逸事趣闻讲一下。遇到一大串不太有名的作者,每个人都这么讲,连篇累牍的,读过以后,满脑子都是“著作郎、知制诰、吏部员外郎、翰林学士、左拾遗、编修、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政事”……一点都不文学,也不具美感。只能说,古代的文人作者大都是官僚体系内的,但实在看不出把他们的\'官位罗列一遍的必要。
虽是吐槽,不过还是很惊叹郑振铎的博学与深厚造诣,他能将不同典籍不同的人诗句、评论信手拈来,将中外的文学历程随心作对比,还费心搜集了一些插图作参照,信息量很大,对于我这个不熟悉文学史的人来说,那么多的没听说过的古代作者的出现,让人发觉在文学的世界里,存在更多的其实是不知名的人物,这让文学史看起来更真实丰腴。
在郑振铎写这本书的年代,战火已起,或是出于强烈的感同身受,他在叙述那些亡国、流亡的作者写的诗词文章时,格外着力,细推和同情他们的飘零之感,如他所述,本书成书不易,他以及友人已然尽了最大的努力,我这无知小辈这样随意点评他的心血之作当是有愧,这份盛在青瓷碗里食材丰富但有点寡味的“羹汤”,已是他能飨客的最宝贵的珍馐了。感佩之极。
推荐中国古典文学的英语作文【四】
围在城里的人想出去,在城外的人想进来,这便是“围城”。这是《围城》中关于人生的论述,《围城》没有哲学上生硬的说教,而是将哲理还原为生活。
小说导读部分有这样的话:“这是一本有趣的书。郑重点说,是本睿智的书,因为它的有趣源自一位智者对人性的洞察与调侃。……在哈哈大笑或含笑、哂笑之时,你会叹为观止,会惊异于作者何以竟能做到这一步。”作者对人世和人性的洞察已经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对人心已经窥探得一览无余。读着《围城》,既能刺着痛处又能挠着痒处,于是我在麻痹中被吸引了。
本书主人公方鸿渐是个留学生,家境中等偏好,于是便有了些公子哥儿脾气。那时候,出国留学已是中国的一大特色,留学生太多。物以稀为贵,留学生这样多已经不值钱,似乎连质量也大打折扣,远不如詹天佑们。方鸿渐虽无蛮横无理的脾性,也不是大奸大恶之人,但他却是个平庸的人。他志大才疏,常满腹牢***,也爱自吹自擂。这样的人经历了求学的艰难,婚姻的困惑,终于明白了:围在城里的人想出去,在城外的想进来。这就是人生的特点。
一本优秀的小说是包罗万象的,无论是谁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影子。我就在方鸿渐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我也似乎是志大才疏,放假时总是无所事事,爱好太多但都不精深,我就是生活中的方鸿渐。我想生活中的方鸿渐还不止我一人。《围城》中有这样一段话:“有九个死掉的自己埋葬在记忆里,立碑立墓。”我也要让现在的自己死掉,让方鸿渐的灵魂从我身上撤走,把死掉的自己埋葬,立碑立墓,不用来悼念,而用来警示,让活着的自己活得更好。我会放弃自己的懒惰和自卑,重拾勤奋与自信。
《围城》中阐述的论点,不得不让人深思,人们一开始对新事物保持好奇心,然而当努力争取到了以后却已厌倦,不能适应它。所以除了我们要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合理的选择外,还要坚持下去,适应下去,包容下去。
《围城》就像一位智者,我们能从他那儿学到很多很多。
推荐中国古典文学的英语作文【五】
相较于学者本人的著述,我更喜欢读他们的学生整理的他们的授课或谈话录,迄今已读过的此类书目有陈丹青整理的《木心回忆录》,韩敬源整理的《观音在远远的山上——伊沙的文学课》,它们都没让我失望,因此,当先生买回来叶龙整理的钱穆先生讲授的《中国文学史》时,我第一时间捧起此书并用三天时间一口气读完,自然,此书一样让我振奋。
家里其实已有很多钱穆专著,连“钱穆先生全集”都有15本之多,但我却一本也没读,心里想的是,以后再读不迟。但他的文学史我却先睹为快,确实因为讲课和著述有阅读上的不同效果。著述,难免要正襟危坐,谋篇布局,遣词造句,就连我写这么一篇小读后感,都要一字一句斟酌一番,学者写文,更要考据引喻,慎思慎言了。而讲课就不同了,能讲得出来的首先得有货沉淀于心以备脱口而出,特别是不依凭讲义而讲述的,更是烂熟于心的思考存积,其价值不可估量。其二,讲课中受到当时当地当情当景的激励,是很能灵光闪现出很多精彩诗思的,这诗思,是连讲述者本人都会被震惊到的。有过讲座经历的人都会有此体验,状态好的话,眉飞色舞,妙语迭出,这,又是冷静伏案写作所企及不到的。读讲课笔记之鲜活,之灵动,是吸引我的重要原因。
钱穆先生是公认的通儒和国学大师,他1894年生于江苏无锡,这值得说一笔。无锡这地方奇了,尽出姓钱的大师,钱穆,钱锺书,钱中文,前两者我不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钱中文老师我曾采访过,问他这钱和钱锺书那钱是否亲戚,答曰,非。但从小,钱中文老师就知道钱锺书先生。我打定主意,下次见到钱中文老师也要问问他是否和钱穆先生是亲戚?钱穆先生和著名科学家钱伟长真是一家,属于叔侄关系。钱伟长回忆叔叔钱穆时说,“他(钱穆)在苏州(中学)任教时,朝迎启明夜半繁星地苦读”,钱穆自己也说,“我认为每个人的天资是差不多的,一个人要写出好文章,最要紧是要多读书,要能刻苦学习”,天资聪颖如苏东坡在钱穆看来也是多读书的典范,钱穆在课堂上说,苏东坡21岁便考中进士,主要是因为他博览群籍、广征博引、多读书喜读书之故。
《中国文学史》是钱穆先生在新亚书院授课时的口述经由他的学生叶龙整理后出版的教材,全书31篇,从绪论到结论,实际就是中国经典文学作品史,或者更具体一点,中国经典文学选本史。以前曾听闻一言,文学史就是选本史,今日读钱穆教材,信了。当然,这也只是文学史之一种。《中国文学史》从诗经、尚书、春秋、论语……一路梳理到明清章回小说,对胡适发起的新文学运动点到为止,全书即告终。我读此书,多次读到眼酸,一种莫名的感动和向往,回望中国传统,不能不肃然起敬。本书灌注了钱穆先生对中华文明的一片赤诚,当他缓慢道来一部又一部经史子集,当他说“胡适不讲道理,只说‘孔教吃人’的口号,而并不说出理”时,我能感受到老先生的无奈和痛心。钱穆先生有很深的孔子情结,他认为,若要大略了解古代文学,《诗经》和《昭明文选》就可以了;他推崇孔子为诸子中之首位,认为《论语》文学价值极高,“更遑论其思想”。钱穆特为《论语》辟出一篇。
读《中国文学史》是对既有阅读的回望,更是对阅读缺失的一种补充。第17篇建安文学,钱穆先生对曹操的解读让我很受益。钱穆注意到了曹操的平民文学之路,虽在政治上跃升为领袖,但作品并无官僚吐属,仍出于私人情怀。曹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挥洒自如,毫无拘束,在钱穆看来,是一代枭雄在文风上的突破。钱穆课堂上的曹操,可亲可近,不似《三国演义》里的曹操,阴险狡诈。
对建安七子大都早夭,钱穆给出的猜测是,“不知是否诗酒应酬过频,以致伤肝病亡”,并进而提醒“这养生问题,实在是我们读书人应该注意之事”。
钱穆自己活到1990年,以96岁高龄仙逝,实在令我辈欣羡不已。钱锺书、杨绛,也都高龄而终,除了无锡这地的风水好以外,中华古籍之于一个人身心的宁静,应也是高寿原因之一。这算是我的猜测。
读《中国文学史》,读到了许多故事,这些故事事关作品和作者,兴许在正史中读不到。譬如欧阳修某年偶寓汝阳,遇见两位活泼歌伎且能背唱他的词,欧公不免心欢,约定将来要来汝阳做太守,再来欣赏她们。数年后,欧阳修果然如愿到汝阳当太守,却不见歌女踪迹,于是怅惘赋诗“柳絮已将春色去,海棠应恨我来迟”。譬如苏东坡某次替人读文章,读后说,该文内容文笔仅仅值一分,他的诵读却占了九分。
类似的名人轶事一定深深藏在钱穆身上,只待时机一到便含笑说出,我们都从学生时代过来,当然很清楚这样的故事是多么活跃课堂气氛,又是多么深入人心。古之贤达真是名士风流,也因此留下很多供后人神往不已的掌故,这些掌故倘无钱穆这样博学的先生传递,很快也会隐没无踪,没有掌故的文学史该多么无趣!
一部《中国文学史》,钱穆先生一直强调,中国传统文学自有其一套生生不息的活的永恒的生命,他反对今日中国自五四以来因有人提倡有了新文学,便认为京剧及以前那些文学都是旧文学。时在1950年代。时代既已走到21世纪,对国学的重视已提上议事日程,当足以慰先生了。
推荐中国古典文学的英语作文【六】
这个假期,我有幸从首都图书馆借阅了林庚老先生着的《中国文学简史》一书。此书近六百页,从史前的诗歌说起一直讲到近代新文学的曙光。伴随五千年的朝代更迭,战火不断,中国文学也走过了从最初的民歌到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多种形式的文学体裁。在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布满荆棘,十分曲折甚至混乱。但是我从中似乎找到了一个隐含的规律:凡是国难当头或是官场不平的时候,文学创作往往会出现高潮,优秀作品批量问世;安定之时倾向于追求程式化写作,没有创新。逆境使人图强,顺境使人堕落。
寒士文学中,屈原为后代文人树立了爱国、与封建贵族阶级坚决斗争的榜样。司马迁、陶渊明、阮籍、嵇康、左思、李白、杜甫、白居易、顾炎武等等……幸福的人大都相似,不幸的人却各有各的不幸。他们遭遇了生活中种种的苦难,这些寒士为无法实现自己理想而在文学作品中长啸、感叹、抒怀、落泪。李白是其中最富有反抗性的,又是最乐观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李白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信念通过他从封建礼教中解放出来的自由的诗歌中体现。“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情景恐怕也只有李白能想得出来吧!比如杜甫,在他沉郁顿挫的诗歌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他对盛唐时期终结的惋惜。“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再比如没落的世家后代曹雪芹写出了千古奇文,把对封建制度的反抗带到深刻的文学作品中,成为四大经典名著,为世人传诵。这些优秀作品无不在逆境中破壳而出,在沉寂令人窒息的政治空气中劈过一声惊雷。
从另一方面看,文章憎命达,政治环境好转,好的文章就不多见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宋朝。宋朝为了抑制军阀势力滋长,广泛吸取文人参与政治,是历朝最重用文人的,寒士的政治抱负实现。整个封建社会乃日益表现为生活上的趋于暮气,文化阶层的走向因循保守,整个朝政笼罩在得过且过、苟且偷生的气氛中,艺术趣味崇尚枯槁老境。于是,韩柳的古文运动也就来得顺理成章,更讲求全面罗列、铺陈,让文章重回古时,文章的赋化趋势再现。顺境使人追求安逸从而堕落。
中国历来就有居安思危的故事,《孟子》中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勾践灭吴的故事成为经典。“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纵观文坛三千载,逆境使人图强,顺境使人堕落屡屡得到印证。如今,在现代社会中的安定也容易让我们在飞速增长的GDP中安乐而死,只有时刻保持危机感,能够自我发现危机和不足,才能保持持续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