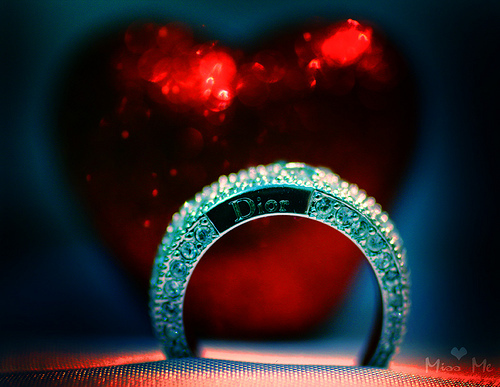
有趣的小鸡作文二年级几句话【一】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和几个伙伴一起去公园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
游戏开始了。老鹰瞪大双眼,凶狠地盯着小鸡。它一会儿扑向左,一会儿扑向右;鸡妈妈张开双臂,一会儿挡到左边,一会儿又挡到右边。突然,老鹰掉转方向,绕过母鸡,向最后一只小鸡扑来。鸡妈妈见情况不妙,大声呼喊,小鸡们有的东躲西藏;有的拼命喊妈妈;有一只吓得站在原地发呆。老鹰见机会来了,猛地冲过去把那只小鸡抓住。
这个星期天的下午,我们都玩的非常开心!
有趣的小鸡作文二年级几句话【二】
星期六中午,我从兴趣班学习回到家。刚到院子门口,忽然听见有“叽叽叽”的叫声,只见六只全身金黄色的小鸡一边叫着,一边向我走来。
为了不让小鸡乱跑,让它们住在一个箱子里,有时候让它们走出箱子自由地活动一下。
小鸡们很活泼,也很顽皮,而它们吃饭时则很有趣。
到了吃饭的时候,我就会用碗取来适量的米粒,然后将米粒慢慢地倒下去。这时小鸡们靠边站着,好象在“避雨”。有时甚至拥挤在一起,都不想接受“米粒雨”的袭击。“米粒雨”下完之后,小鸡马上吃起来,犹如在跟同伴比赛谁吃得多。它们先低下头,用尖尖的嘴巴啄米粒,啄了几粒,再咽下去。小鸡吃饭的时候也需要水。我拿着一个小碗,盛上水,然后小心翼翼地放到箱子里。小鸡吃了一些米粒,感到口渴的时候,它们就低下头,将尖尖的嘴插入水中,含上水后仰起头,脖子稍微扩大了一下便咽了下去。
有一天,小鸡们离家出走了。好心的邻居捡到了,就给我们送了回来。他们的孩子也很喜欢小鸡,我就送给他们两只。
后来,陆续有小朋友向我们要小鸡,我又恋恋不舍地将剩下的小鸡一一送人了。
有趣的小鸡作文二年级几句话【三】
周日老师带我们去动物园里看猴子。我们来到猴山前一看,嗬!里面有十几只呢!
猴子都是红脸、红屁股,全身土黄色的短毛。不同的是,有的个头大,身体强壮。有的瘦长,还有的小巧玲珑十分可爱。
游客们将手中的水果扔进去,十几只猴子纷纷赶来哄抢。往往都是那只个头最大,长得最强壮的猴子抢到最多。别的猴子好像都怕它,没几个敢跟它抢。有几只大块头耐不住水果的诱惑,跃跃欲试地想上前来抢,最后都被那只壮硕的猴子给吼跑了。老师告诉我们,这位胜利者就是 猴王 。 猴王 带着它的战利品,慢条斯理地爬上猴山,坐在上面霸气地独享抢来的美食。
其余的猴子很快就忘记了抢不到水果的苦恼,各自玩耍起来。有几只较小的猴子坐在猴山底下晒太阳、挠痒痒,其中一只把吃完的香蕉皮顶在头上当帽子,样子真好笑。有几只特别活泼的,在猴山旁的树上抓住树枝荡秋千。一只特别小的猴子,把吃剩的桃核扔来扔去地玩,自得其乐。
时间不早了,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恋恋不舍地离开猴山。再见可爱的小猴子们,下次我还要和爸爸、妈妈一起来看你们。
有趣的小鸡作文二年级几句话【四】
在一个春天的早晨,郊外的路边嫩嫩的小草上有着晶莹剔透的露珠。清澈见底的小河“哗哗”地流着,好像在欢乐地歌唱。旁边的小树正在忙着发芽,后面的草丛正在忙着开放。
小鸡叫小鸭去散步。走在路上,小鸡和小鸭边聊天边散步。它们聊着、聊着,小鸡骄傲地说:“你看我的帽子多漂亮。”小鸭不服气地说:“你看我的帽子才漂亮,你的一点都不好看。”小鸡急忙说:“我的衣服比你的帽子更漂亮。”小鸭又说:“你看我的鞋子比你的衣服更漂亮,还有你就没有穿鞋。”刚说完,忽然,风呼呼的刮起来。小鸡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小鸭伸长了脖子,张大了嘴巴,特别吃惊。一会儿,风停了,小鸡的帽子被刮进了河里。小鸭的帽子被刮到了树上。小鸡恐惧,着急,来回渡步。小鸭急忙踮起了脚尖,脖子伸长。但小鸭怎么够都够不着。一会儿,小鸡想了一个妙招。对小鸭说:“你会游泳,你帮我把我的帽子捡回来。我会飞,我把你的帽子捡回来好吗?”小鸭说:“好呀!”小鸡拍了拍翅膀飞上了树梢,帮小鸭捡回了帽子。小鸭跳下水里也帮小鸡捡回了帽子。
它们拿着对方的帽子,互相还给了对方,并互相道谢!
有趣的小鸡作文二年级几句话【五】
一年前回上海来,对于久违了的上海人的第一个印象是白与胖。在香港,广东人十有八九是黝黑瘦小的,印度人还要黑,马来人还要瘦。看惯了他们,上海人显得个个肥白如瓠,像一代乳粉的广告。
第二个印象是上海人之“通”。香港的大众文学可以用脍炙人口的公共汽车站牌“如要停车,乃可在此”为代表。上海就不然了。初到上海,我时常由心里惊叹出来:“到底是上海人!”我去买肥皂,听见一个小学徒向他的同伴解释:“喏,就是张勋的勋,功勋的勋,不是”薰风的薰。《新闻报》上登过一家百货公司的开幕广告,用并散并行的阳湖派体裁写出切实动人的文字,关于选择礼品不当的危险,结论是:“友情所系,讵不大哉!”似乎是讽刺,然而完全是真话,并没有夸大性。
上海人之“通”并不限于文理清顺,世故练达。到处我们可以找到真正的性灵文字。去年的小报上有一首打油诗,作者是谁我已经忘了,可是那首诗我永远忘不了。两个女伶请作者吃了饭,于是他就做诗了:“樽前相对两头牌,张女云姑一样佳。塞饱肚皮连赞道:难觅任使踏穿鞋!”多么可爱的,曲折的自我讽嘲!这里面有无可奈何,有容忍与放任——由疲乏而产生的放任,看不起人,也不大看得起自己,然而对于人与已依旧保留着亲切感。更明显地表示那种态度的有一副,是我在电车上看见的,用指甲在车窗的黑漆上刮出字来:“公婆有理,男女平权。”一向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由他们去吧!各有各的理。“男女平等”,闹了这些年,平等就平等吧!——又是由疲乏而起的放任。那种满脸油汗的笑,是标准中国幽默的特征。
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
谁都说上海人坏,可是坏得有分寸。上海人会奉承,会趋炎附势,会混水里摸鱼,然而,因为他们有处世艺术,他们演得不过火。关于“坏”,别的我不知道,只知道一切的小说都离不了坏人。好人爱听坏人的故事,坏人可不爱听好人的故事。因此我写的故事里没有一个主角是个“完人”。只有一个女孩子可以说是合乎理想的,善良、慈悲、正大,但是,如果她不是长得美的话,只怕她有三分讨人厌。美虽美,也许读者们还是要向她叱道:“回到童话里去!”在《白雪公主》与《玻璃鞋》里,她有她的地盘。上海人不那么幼稚。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包括《泥香屑》、《一炉香》、《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琉璃瓦》、《封锁》、《倾城之恋》七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
我喜欢上海人,我希望上海人喜欢我的书。
有趣的小鸡作文二年级几句话【六】
有一次,我上菜场买菜,发现了一个纸箱,纸箱里有刚孵出来的\'小鸡,它们在里面拱来拱去,毛茸茸的,像黄色的小绒球,真可爱。我就拿买菜的钱买了一只。我小心翼翼地用双手捧着,可它使劲儿在我手心里蹦。我怕蹦出来摔着它,就用衣服兜着,在路上,我在想小鸡的生活习性,它专门吃小米,而且要温暖,我一路小喝总目回了家。
一回到家我找来一个纸盒子,垫上沙子,把小鸡放在里面,还盛了一盘小米放进去。小鸡缩在纸盒的角上,一动也不动。它是不是认生呀我只好把门关上,透过门上的下班悄悄地看着它,它还是一动不动。我想,它可能是累了,睡一觉就好了。
下午一学完象棋,我可不像平日在下面和小朋友一起玩,而是跑回家看刚买的小鸡。但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可爱的小鸡趴在角落里连头都不抬起来。我很伤心,小鸡呀小鸡,你仅仅在我家呆了半天就死了,太可怜了。我想,小鸡死的原因是什么?是被冻死的?还可能是它才这么小就和自己的亲身母亲分离了?应该是被冻死的,我们给的温暖不够。我觉得自己非常浪费,因为小鸡只在我家待了半天就死了。
我吸取了这次教训,以后再也不买小鸡了。因为小鸡太难养一,我根本没空照顾它。
有趣的小鸡作文二年级几句话【七】
前不久,我从姥姥家带回一些五颜六色的小鸡。
小鸡毛茸茸的,像一个个五彩缤纷的小绒球。我在箱子里抓起一只,放在手上仔细观察:小鸡的头圆圆的,两只小眼睛又黑又亮,像两颗黑宝石似的;它们的嘴巴是鹅黄色的,像一把利剑。
小鸡吃食时的样子有趣极了:我把小米洒在地上,他们唧唧喳喳的,争着用嘴一粒粒的啄个不停。
小鸡吃饱后便挤在一起休息,远远看去,就像个五彩的大绣球。
我把小鸡放出来,可捉回去就不像捉出来这么容易了。它们东跑西奔,可真不好抓。突然,我灵机一动,想出了个好办法:把小米撒在小鸡的窝旁不就可以把它们引过来了吗?我快速地把小米撒在小鸡窝旁,一只小鸡果然中了我的计,我迅速把它抓回了窝。用这个办法,我把剩下的小鸡都抓了回了它们的“家”。
因为一共有四只颜色不同的小鸡,所以我按它们的颜色起名:小红、小绿、小蓝、小黄。
我爱这些小鸡,但愿它们能健康快乐的成长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