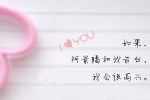散步时光作文400字【一】
宗白华认为“美感的养成在于能空,对物象造成距离。”强调“隔”在美感上的重要,这大概就是所谓“距离美”。朦朦胧胧隐隐约约,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确能产生独特的意境,引人遐想万千。这是空间上的“隔”。至于时间上的“隔”,我想起曾看过的一篇文章,讲印度人约会非常散漫,极不守时,让别人在约定时间后等上一两个小时是常有的事-而印度人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对,照他们看来,等待是一件乐事。在等人时,可以有无尽的想象,想象对方的容貌和表情,想象见面时的亲热和愉悦,何乐而不为。当然这对于严谨的德国人来说没准会被认为是对他们的不尊重。宋人赵师秀有诗“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一幅悠闲淡然的图景。与朋友约好下棋,等到夜半朋友还没到,便独自敲着棋子,挑下灯花,却不显得惆怅,这大概也是等待时想象的快乐吧。“时间”与“空间”上的“隔”都给艺术增添了想象的成分,而这想象又造成心灵的“空”,也成艺术的空灵。王国维所说的“隔”则是指诗词中的生僻词句典故,不懂这些词句典故便不能领会作者表达的意思,这就使观者产生隔离感(往往不是距离美),这种隔离感不是想象可以弥补的,除非去查资料,而这样就容易导致阅读的不连续,破坏了意境的营造。这大概也是王国维反对“隔”,提倡“不隔”的原因。因此并非所有的距离都能产生美,它应该处于合适的范围内,既不是完全如一的现象还原,也不至于大到不可捉摸,无可名状。合适的距离才能使艺术空灵而不流于空乏,充实而不至于挤兑想象的空间。“一个艺术品,没有欣赏者的想象力的活跃,是死的,没有生命的。”(39页)艺术家需要想象创作,艺术品也需要欣赏者的想象才能达到最大的升华。
散步时光作文400字【二】
夜晚来这里散步,最让我喜欢的就是这满眼的绿色。
这里有各种各样的植物,有高大的树木,也有矮小花草,还有长长的青藤,一簇一簇的灌木。他们的叶子也是形状各异,但只有那绿色是一样的。让眼睛看起来,那样的舒服和愉快。做一个深呼吸,空气中有淡淡的特殊的味道,就是那些叶子发出来的吧。
沿着山间小道,穿行在这些绿色中间,感觉自己就是一只小兽,或者善于奔跑和跳跃的小动物。在密密的树林中穿行,可以两足行走,也可以四肢行走,还可以学着猴子的样子,爬上一颗大树,打着眼罩远望,甚至可以学着各种动物的声音,吼几声,宣泄一下久憋在胸中的怨气。
遇到了一片平整的草地,这软软的天然的地毯,干脆躺在上面打起滚来,完全的放松自己,让自己重新变成一个孩子,忘记刚才在城市里的烦躁和名利。甚至可以忘记回家的路,就呆在这片草地上,与一只虫子做邻居,今晚,听着他们的歌声入眠。
等到站在一个高高的山头上,自己变成了最高的巨人。俯视远处的城市和乡村,感觉自己茅塞顿开,仿佛自己是能给予时间万物恩泽的主宰者,好想把自己最美好的祝福都献给天下所有的苍生。更感觉到自己的渺小和世界的博大。
不过,感觉最快乐的,还是变成一只鸟儿,就是变成一只小小的飞虫也好,只要能带着翅膀,只要能飞翔。我就会自由自在地在这绿色的海洋上空盘旋,一会俯冲,一会升起,一会隐没在这绿色之中。
其实,绿色代表的是一种生机勃勃的力量,一种自然的和谐与美丽。还有在绿色之中,孕育的无数的生灵和奇迹。我们可以喜欢绿色,我们必须保护绿色,保护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后代,永远有绿色的眷顾与保佑。
散步时光作文400字【三】
一般说来,将拉奥孔的嘴巴雕刻得张大或微开显然不会过多影响人们对创作者的能力的评判。观众评价这件艺术品是按照内心所获得的感受,即以是否产生或产生何种程度的审美愉悦感来评价它的优劣程度,进而以此评价创作者的能力。假设有两座拉奥孔的雕像,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微开着嘴巴的拉奥孔比张大嘴巴的拉奥孔更能激起人们的美感(理由见《美学散步》6-7页 莱辛语),人们便认定前者更有艺术性,而将拉奥孔的嘴巴雕成微开状的那位创作者更富有创作才能。在此条件下,便可以说,艺术反映人的能力。“艺术是一种技术,古代艺术家本就是技术家”(24页)讲的也是这个意思。
“美是艺术的特殊目的”,“艺术”的一定是“美”的,“美”的却不一定是“艺术”的。因为“艺术”反映的是人的能力,那些未经人加工的自然状态下的事物、风景,就不是“艺术”-虽然它们也会使人产生美感。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指出:“如果说荀子强调的是‘性无伪则不能自美’;那么庄子强调的却是‘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虽然艺术必然是人为的(有人的因素在其中的),然而前者(荀子-儒家)“强调艺术的人工制作和外在功利”,后者(庄子-道家)“突出的是自然,即美和艺术的独立。”我认为此处道家所强调的“自然”,应归因于对过分“人为”的纠正,即认为艺术不能囿于狭窄实用的功利框架。至于“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我认为这种“大美”不能被称为“艺术”。我们看到无垠的天、广阔的地、瑰丽的晚霞、壮美的山川时,不会认为它们是“艺术品”,虽然也会由衷地感叹它们的“美”。“艺术品”必然是人为的,是人加工过的.东西。若说某座山“鬼斧神工”,那只是将“造物主”拟人化了,反映的还是人的能力。若将这些天、地、晚霞、山川绘成图画、拍成照片,那便成为艺术品,因为图画、照片才反映人的能力,而事物本身-未经人加工过的-并不是艺术品。因此庄子所说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说的是天与地使渺小的人产生的“崇高感”,这是自然地会在人心中产生的“美感”,我们不必牵强地认为在人类诞生前早已存在的天与地是“艺术品”,虽然它们确是“美”的。
“诗和春都是美的化身,一是艺术的美,一是自然的美。”(14页)这已经很好的说明了“艺术”与“自然”的区分了。
“艺术须能表现人生的有价值的内容?必须同时表现美(7页)”,这一点可以从美就是有价值的东西这一层面来理解。有用的不一定都是美的,苏格拉底所说的“粪筐也是美的”之所以不被认同,在于有用的东西还需引起人的愉悦感,才能被称为美的。
艺术创作可以遵循规律,也可以突破规律。如既有对称美,又有不对称美。但“表现人
生的有价值的内容”和“表现美”却是艺术所必须具备的,失去其一,便不能成为艺术。 宗白华在引用莱辛的话中有这样一段:“文学追赶艺术描绘身体美的另一条路,就是这样:它把‘美’转化做魅惑力。魅惑力就是美在‘流动’之中。因此它对于画家不像对于诗人那么便当。画家只能叫人猜到‘动’,事实上他的形象是不动的。因此在它那里魅惑力就会变成了做鬼脸。”但是在文学里魅惑力是魅惑力,它是流动的美,它来来去去,我们盼望能再度地看到它。又因为我们一般地能够较为容易地生动地回忆‘动作’,超过单纯的形式或色彩,所以魅惑力较之‘美’在同等的比例中对我们的作用要更强烈些。”(9-10页)在中国画里,同样地,绘画(艺术)可以将文学里的难以追逐的“美”转化做“魅惑力”。就意而言,与画相配的诗并不一定具有“明确表达的含义”,如王维的《蓝田烟雨图》所配的诗,它表现的意境既与王维的诗意相似又不尽相同,看上去是阐释了诗,实际给人的感觉又是增添或模糊了画面原先并不具有的意味。也就是说,这首诗既是一种阐释和理解,又是一种再创作。不同的诗人可能因对这幅画有不同的而写出不同的诗句,不同的画家也会对此诗有不同的体会而画出不同的画来-新创作的画又会表现出新的意境,由此诗配画,画配诗,延绵不绝。这也可以说明诗与画并不是一回事,却是可以圆满结合,“相互交流交浸”,以至交融完满的。
散步时光作文400字【四】
其实,我认为《散步》的情是淡的,但它让人品味到的,是最让人动情的。
有时候人并不明白,为什么一次散步,一束鲜花,一个微笑能带给父母或长辈那么多的愉快。只有一个人人都为他人的家庭,才真正幸福。,就不会有家庭纠纷,离婚等惨剧。人应该是能将心比心的,只有这样,人们才能不吵架。但我又何尝不应该如此呢?唉,我曾带给父母多少喜,多少忧啊!
但就算我不这样,又能如何呢?老实说,真的,我有些叛逆。我为此苦恼不已,只有挫败才能带个人经验,我是不懂的,就算我能讲出个道道来。也许我要经过十几年才能真正懂啊!人生无常,父母又能陪伴我们多少时候呢?我一定要珍惜这时日了!
人生苦短,我的生命有限,但我要让它更有意义!
散步时光作文400字【五】
《散步》是一篇清新优美的散文。它像一首动人心弦的诗,一支感人肺腑的歌,颂扬了我国人民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反映了我国文明家庭建设的可喜成就。
文章在选材上颇有特色。作者深深懂得一滴水可以辉映太阳的光辉的道理,精心选材,以小见大。文章只是选取一个三代同堂的家庭一次散步的小事来写,就表现了一个重大的主题:中华民族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在新的时代得到了发扬光大。
在这个三代人的家庭里,我处于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每当家庭出现分歧的时刻,我总是主动地站出来,消除分歧,维护团结,增进亲情。我家要到田野上散步,可是母亲不想去。原因是母亲老了,身体不好,好不容易才熬过了一个严冬,走远一点就觉得累。母亲的想法并非毫无道理,但是我不是消极的表示顺从,而是积极地提出建议。我劝说母亲,正因为年老体弱,才应该多走走。我的话渗透着辩证思想,饱含着对母亲的深切的爱,有利于母亲身体素质的增强,有利于家庭温馨氛围的营造。母亲听了我的话,不是固执己见,而是从善如流。儿子敬爱母亲,母亲尊重儿子,家庭出现了融洽、祥和的气氛。
家庭犹如一口池塘,有时波平如镜,有时波浪起伏。在散步的过程中,这个三代之家就像平静的水面涌起了波澜。在岔路口,我的母亲要走大路,我的儿子要走小路。大路平顺,便于老人行走;小路难行,可是秀色可心。在鱼与熊掌不可得兼的情况下,我决定舍鱼而取熊掌。我认为,母亲年老体弱,余年不多,伴随她的机会已很少;儿子年纪尚幼,来日方长,伴随他的机会还很多。于是我委屈儿子,顺从母亲,作出了走大路的决定。这个决定是明智的,体现了中华民族尊老的美德。
就在我作出了走大路的决定的时刻,母亲忽然摸摸孙儿的小脑瓜,改变了主意:还是走小路吧。母亲疼爱孙儿,了解孙儿的心思,知道孙儿喜欢小路旁边金色的菜花,整齐的桑树,小路尽头水波粼粼的鱼塘,于是决定自己克服困难,满足孙儿的心愿。母亲改走小路的决定,体现了中华民族爱幼的传统美德。
小路不好走,母亲对我说:我走不过去的地方,你就背着我。到了一处难走的地方,我蹲下身子,背起了母亲;妻子也蹲下来,背起了儿子。他们怕摔伤了自己所背的亲人,因此走得很慢,很稳,很仔细。他们的行动体现了中华民族尊老爱幼的美德。
散步时光作文400字【六】
“意境是艺术家的独创,是从他最深的‘心源’和‘造化’接触时突然的领悟和震动中诞生的,它不是一味客观的描述,像一照相机的摄影。”(79页)这说明了绘画(艺术)与照相机的区别。摄影所得的照片记录的只是一种机械的真实,将一瞬间的光与影定格下来,在这一意义上说,照片比绘画更能反映现实,它几乎是丝毫不差(差别的只是精度)地记录下真实的场景,将现象还原至本来面目。绘画若在这一点上与其一较短长,必然技艺不如。这也许是十九世纪以来写实主义绘画不在占据主流的原因之一。中国传统山水画论认为“似
者得其形,遗其气,真者气质俱盛”,崇尚“气韵生动”。这种“气韵”并不是虚幻而与现实毫无瓜葛的,这种“真”同样要求“对自然现象作大量详尽的观察和对画面构图作细致严谨的安排。”(李泽厚:《美的历程》 169页)中国五代画家荆浩惊异于太行山之美,作了数万本草图,“方得其真”。这种“真”自然不是简单的真实,画家在作画时,每一刻的心绪都不同,每一笔都是不同心绪的反映,绘成整体便是无数不同心绪的集合。可以说绘画既是空间(平面)上点﹑线﹑色彩等的组合,又反映了时间上的心理凝积过程。在这一意义上说,一幅画包含了无数幅画,是无数个心理活动凝积的产物。因此画是“流动”的,即“美在流动之中”(9页)。
或认为就算摄影所得的照片不是“流动”的,那么录像总该是“流动”的,它真实记录了事件的前后过程,应该是最真实的“真”。我认为录像只是有限张(或者无数张)照片的连续展示而已,它在本质上仍然是相片,仍然只是机械的真实。无论多长的录像,它总是有限的(时间和空间),注定它不能反应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一幅画或许只描绘了一幅图景,却可以蕴藏着无限的刹那,而相片虽然也可以让人联想,却因为它过于形象,反而或多或少剥夺了欣赏者想象的权利,想象的空间丧失了,艺术性也就随之削减了。
摄影的过程是机器的运作,只能反映“物理的目睹的实质(85页)”,绘画是画家用画具混合了自己的心绪、情感、记忆创作出的给欣赏者以无尽想象空间的艺术品。这也许已经决定了二者在艺术性上的区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