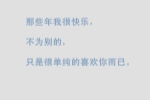雨天上学小学作文【一】
在我的记忆中,风风雨雨,晴晴阴阴的天气数不胜数,如同星罗棋布的石子,留在我的记忆长河中,那个雨天既平凡,又不同寻常,给我留下了永久的回忆和终身的启示。
那一天就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别看上午还阳光明媚的,下午在突然之间就电闪雷鸣,狂风大作,倾盆大雨。马上就放学了,我不禁皱着眉头,发起愁来。望着窗外的倾盆大雨,我叹了一口气背着书包向外冲,我已经做好了一只落汤鸡的准备,不料却迎面撞到一个人,我抬头一看,原来是妈妈。只见妈妈一手拎着包,一手举着雨伞向我们班跑来脸上充满了焦急,几颗雨珠顺着她那乌黑发亮的头发留下来。妈妈一见到我就说:“孩子,你没淋着吧!咱们快回家吧!”一路上,妈妈总是把雨伞往我这边推,我说:“妈妈,您怎么总是把雨伞往我这边推呀?您都淋湿半个身子了。”妈妈强装着笑脸说:“妈妈没淋湿,真的!”我心头一热。这时一阵冷风吹过,妈妈打了个哆嗦。我的脸上分不清是泪水还是雨水……
多少年来,我认为一个热情的拥抱,一段甜蜜的语言,一次快乐的陪伴都是母爱。今天,我终于明白:爱是无声的,无形的,是用金钱所买不到的。母爱比山高,比海深,它比父爱更慈祥,比师爱更深沉,它不愧为世界上最伟大、最真挚的爱!
雨天上学小学作文【二】
喜欢下雨,仅是精神上的喜欢而已,肉体上的我就不敢当了。所以我并不像某些爱雨之人,当下雨时,欢喜到连雨伞都不带,就去和雨水来个“亲密接触”。我可没有这样的勇气和体魄,如果因此而患了重伤风或感冒,还要掏钱去医治。
所以呢,我只是站在阳台上,静静地看着窗外的雨点打在屋顶,打在地上,打在过往行人的头上……然后,我再用双耳去聆听这雨水所唱的'歌。可是,无论我怎么去听,我始终也不能听出雨水到底在唱些什么,但我不死心,仍想用我的耳朵来捉摸雨的想法。有时候,我或许会伸出双手,让雨水拍打在我的手臂上;又或者有时心血来潮,就用双手盛住飘落的雨水,用我的口来品尝一下到底雨的味道是什么……
与下雨前不同,雨后的空气总是非常清新,仿佛大地就像刚被洗涤一样。洗涤?对了,或许雨水唱的正是洗涤之歌。它要洗去这个世界的肮脏,冲走空气中的污浊,洗涤我们的灵魂。虽然最后得到的并不是长久性的结果,不过雨水很满足,因为它曾经来过这里。
又下雨了,我的灵魂再一次被洗涤。也许雨水不一定能洗去我心中的污浊和肮脏,可是,我却乐于接受这一切。
雨天上学小学作文【三】
一清早,掀开窗帘看看,窗上已撒满了水珠;啊,好极了,又是个下雨天。雨连下十天、半月、甚至一个月,屋里挂满万国旗似的湿衣服,墙壁地板都冒着湿气,我也不抱怨。雨天总是把我带到另一个处所,在那儿,我又可以重享欢乐的童年。
那时在浙江永嘉老家,我才六岁,睡在母亲暖和的手臂弯里。天亮了,听到瓦背上哗哗的雨声,我就放了心。因为下雨天长工们不下田,母亲不用老早起来做饭,可以在热被窝里多躺会儿。我舍不得再睡,也不让母亲睡,吵着要她讲故事。母亲闭着眼睛,给我讲雨天的故事:有个瞎子,雨天没有伞,一个过路人见他可怜,就打着伞送他回家。瞎子到了家,却说那把伞是他的。他说他的'伞有两根伞骨是用麻线绑住,伞柄有一个窟洼。说得一点也不错。原来他一面走一面用手摸过了。伞主笑了笑,就把伞让给他了。
我说这瞎子好坏啊!母亲说,不是坏,是因为他太穷了。伞主想他实在应当有把伞,才把伞给他的。在熹微的晨光中,我望着母亲的脸,她的额角方方正正,眉毛细细长长,眼睛谜成一条线。我的启蒙老师说菩萨慈眉善目,母亲的长相一定就跟菩萨一样。
雨下得越来越大。母亲一起床,我也跟着起来,顾不得吃早饭,就套上叔叔的旧皮靴,顶着雨在院子里玩。我把阿荣伯给我雕的小木船漂在水沟里,中间坐着母亲给我缝的大红「布姑娘」。绣球花瓣绕着小木船打转,一起向前流。
天下雨,长工们不下田,都蹲在大谷仓后面推牌九。我把小花猫抱在怀里,自己再坐在阿荣伯怀里,等着阿荣伯把一粒粒又香又脆的炒胡豆剥了壳送到我嘴里。胡豆吃够了再吃芝麻糖,嘴巴干了吃柑子。大把的铜子儿一会儿推到东边,一会儿推到西边。谁赢谁轮都一样有趣,我只要雨下得大就好。下雨天老师就来得晚,他有脚气病,穿钉鞋走田埂路不方便。老师喊我去习大字,阿荣伯就会去告诉他:「小春肚子痛,睡觉了。」老师不会撑着伞来找我。母亲只要我不缠她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