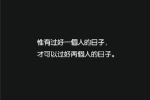专升本大学语文议论作文【一】
然后,我就痴迷上了篮球比赛。那时候因为姚明大家都喜欢火箭队,我也喜欢火箭队,不过我最爱T-MAC。即使与科比相比,他不够柔美;与詹姆斯相比,他不够霸气;与艾弗森相比,他不够灵动。他的职业生涯是不匹配他的天赋的,连续的带队止步于季后赛首轮,我都自做多情的觉得不好意思了。在前年的总决赛第六场,当雷阿伦射进那个三分球后,我竟控制不住夺眶而出的眼泪,因为他或许永远都不可能染指总冠军了。他确实不够勤奋,不够争气,只是,只有他是那个独一无二的T-MAC。
小学只是看球。那时的小学是平房,残缺的水泥操场上只有一个孤零零的固定篮架。它的篮板是木制的,上面的油漆掉了好几块,篮筐生着锈且摇摇欲坠。没有人会有往那个篮筐里扔篮球的***,扔石子的倒是不少。不管怎样,校区重建时,那个篮架总算被拆掉了。记得有一次,我走路时盯着一个大一届的女同学看,还一头撞在了水泥篮架上,成功的搏到了那名女生的注意力。
童年的时光总是拿来飞的。我就屁颠儿屁颠儿的走进初中校园了——一个离小学两百米的地方。屁颠儿的我以为这下终于可以在篮球场上打球了。神秘的初中啊,有一个完整的篮球场,按辈分使用。初三的那班人打球,初二的那班人,初一的我们只有一边看的份。于是,我就发动村里的小伙伴们筹钱买了一个迷你篮板,把它钉在房子外面的支柱上,做了一个小小的篮架。当时在村子里,我的篮球水平最高。比我高的技术没我好,比我矮的自然打不过我,我们一共有四个人。我那时候的运球技术确实还不错,体育课的时候,我可以一直胯下运球从球场一边运到另一边,而且我的转身也很帅。在当时,打球帅是一个吸引女生注意的`大招。我也就偶尔一个人在一边默默的秀运球,总感觉有一大班女生盯着我看,我不好意思起来,就一直低着头运球。事实证明:当时我很可能只是感觉而已。
我的第一个篮球是我的母亲买给我的,是一个兰华的橡胶球,很硬,害我吃了不少“萝卜”。打了一段时间后,球的表面变得软了一些,这个阶段的球是手感最好的,再打一段时间,球的表面就会变光,变滑,球也容易起包。初中三年,我一共买了六个球,清一色橡胶球,五个兰华,一个别的牌子的。那时候,打牛皮篮球是一件很拉风的事,同村的一个小伙伴就买了一个斯伯丁真皮篮球(他爸爸是村长)。那个球或许是我目前为止打过的最好的球了,因为那个球真的非常舒服,我发誓,我后来从来没有打过那么好的球了。
初中有一个班主任是全校的体育老师,确实很不可思议,不过这个体育老师真的成了我们的班主任。全班的男生都很高兴,因为觉得这样一周的体育课就会变多了,全班的女生也很高兴,因为这样就可以看×××打篮球了,当然不是,我也不知道女生体育课都干嘛。那个时候,我们打球真的很疯狂。我们往往下课十分钟就到操场打球,吃完早饭打一会儿,吃完午饭打一会儿,吃完晚饭打多一会儿。吃完饭就打球,我因此落下了胃病。教室里常常弥漫着一股汗臭味,男生上课基本都是气喘吁吁的。这个体育老师看我们打球打的这么热火朝天,竟然常常取消体育课改为自习,一周的三节体育课只会有一节。为此,班上一名男生还和他打了一架。打过架后,我们班就常常没有体育课了。
我的母亲给我买篮球,我的姐姐常常给我买篮球报纸——《篮球先锋报》。直到现在,我也会偶尔去图书馆三楼看《篮球先锋报》。当然,姐姐还在上学,不可能每期都给我带。我就省吃俭用,托去县城上课的学长帮我带篮球报纸。无论哪种篮球报纸,都会附送一张“精美”海报,这些海报贴满了我过去房间的墙上,贴不下的送给村里的小伙伴们。那么多海报,真正称得上“精美”的只有一张。那是我最喜欢的一张海报,是买《扣篮》杂志附送的超大“麦迪扣篮”的海报。我把它贴在了门上,这样就能常常看到。到了高中,我自己终于去县城上学了,也终于可以自己放肆的买篮球报纸了,结果到了高三,我家堆得篮球报纸比高三一年做的试卷还多。学业上的压力使得我不可能再做“长大能够打球赚钱”的白日梦了。当然残酷的现实也起了重要作用:我长了一米七,体重一百二十五斤,垂直起跳高度四十厘米。高考的那一年,我做的最多的是,晚上大伙儿卧床聊天时,给室友讲一段NBA历史,室友说:××,听你讲这些真的很起劲呀!都可以和解说媲美了。这是我听过的最好的褒扬了,我真的很感谢一起奋斗的室友们。
时间回到现在,我学习的这门选修课叫:篮球裁判与赛事欣赏。我关注了很多关于篮球的,却发现自己偏偏没有关注过裁判。更多、更深的认识是:篮球、其实是一门学问。我还仅仅停留在最浅层,而我的篮球情怀也仅仅停留在了“喜爱”的层面了。以后,我还将不停地接触篮球,而这种淡浅的情怀也将长驻心中。
专升本大学语文议论作文【二】
古训:“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曾在古代盛行,现在的时代不是不需要这样的古训了,而是在“唯有读书高”这句上,我个人在思想观念上存在一些想法。
当代大学生“上大学存在风险”,不是你上了大学就进入了保险箱,也不是你今后的前程光芒一片,只能说是你为今后谋得更好的前程增加了一个法码罢了。当今社会“就业形势”不是已证了此事了吗?比如,扩招之后,各所大学都在扩招本土及外地生源,好象一夜之间,中国的大地上一下子就都成了高级知识分子似了,什么硕士、博士等等人们都在学历上增长,在学时上有待考究。专科、本科学历的“大学生”好象是小学生水平,在就业市场上好象难谋到理想的职业,现在不是有的大学毕业生在竟聘“卖猪肉”的职位吗?这不就是“上大学存在风险”的真实版本吗?如果你不上大学,只有初中或高中文化水平“卖猪肉”不就可以了吗?何必投入那么多精力、财力,最终还得回到残酷的现实中来与那些生活底层的人们争职位?现如今不得不让我重新审视读大学的风险,这就是我想到的“上大学存在风险”的观点。
初看这是对大学生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否定,细想一想,其实不是这样的,从现实生活中的大学生择业上看,我的观点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有些道理的。
我个人认为也有的单位重学历,轻水平的也不乏有之。学历层次的递增是件好事,但不能只停留在原有的工作水平上,而是真正能成为学历与自身素质同时提升,更不能在学术上搞“天下学术是一家,你评我我评他,最终评的是一家”上,学术上,搞形式与内容的脱节更不可取。让风险也应存在于学术领域,让真正有学问的`人为祖国出更多的学术精品。
有的学生虽是投入金钱,为的是求得功名,到三至几年求得了博、硕毕业证,有工作单位的还好,回到原有单位会要求相应的待遇。苦了那些还在路上狂热的大学生们。
最让人们担心的是今天的就业形势,那就是大学毕业生遍地开花,有的大学毕业生又重新拿起书本,在向更广更深的知识层面进发,最终能否修成正果,读书风险是否在加大未知。也有的大学生先选择了不理想的就业岗位,先择业后选岗位这是当代大学生的明智性的选择。普通的大学生毕业后就面临失业的大有人在,是现实的无奈还是读大学的风险在加码呢?不得而知。
现在有的大学生虽然大学毕业了,最起码的个人简历都不会书写,更谈不上专业知识能力的潜在危机了,虽说是时代变了,但知识能力没有风险呀,投入越多收益越多吗?多数学校是盲目招生,学生到校后,不能得到良好的教育,读大学生风险不是不存在,而是先投入风险,后收获成功的喜悦。
综上所述,“上大学存在风险”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最后让我们的大学生在“风险”中前行,道路虽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让我们伴着国家发展的希望曙光,在人生的决择中,大学生都有一个好的前程、好的归宿。
专升本大学语文议论作文【三】
1.本体论的提问与构成论的回答
语文是什么?我们的回答有许多种:语言+文字,语言+文章,语言+文学,语言+文化。历来的争论大致上都是在“文字”“文章”“文学”和“文化”之间的选择或权重的分配上。从来没有人想过,“语文是什么”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A+B用这种回答方式是关于“语文是什么”的问题的回答吗?
这里,我们需要区别两个概念:本体与构成。
语文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是一个语文本体论的问题,它要回答的是,语文的本源与实质。而A+B这种回答方式,则是一个语文构成论的回答方式,它所回答的,是语文有哪些成分和要素。
语文本体论,属于语文教育哲学的范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构成一个人的语文观;语文构成论,属于语文课程论的范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一个人的语文课程观。如果说语文的本体论设问所期待的答案是“语文是什么”,那么,语文构成论设问所期待的答案则是“语文课教什么”。这两个问题处在不同层次上,它们的答案,也处在不同的领域。
从研究方法上来讲,语文本体论是一种认知思维,它需要的是思辩。它首先要确定人的实践系统,然后弄清楚语文在人的实践系统中所处的位置,以及与其他实践系统的关系,最后才能对语文的本源与实质作出判断。过去,我们试图用释名的办法来获得答案,要么是求之于训诂,要么是求之于“语文”名称发明人的约定;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求之于语文教材或语文课堂教学的实际。这都不是语文教育哲学的研究方法。训诂法也好,考证当事人的约定也好,从教材或语文课堂教学的实际中总结归纳也好,都是证实的办法。这种办法把语文教学当作一种“客观实在”而不是当作一种“实践设计”来看待,陷入了一种以实体证明来探寻本源和实质的路子。语文教育首先是人的一种实践活动,它的本源和实质,是人的一种价值选择。忘记这一点,永远也无法获得关于语文本体的说明。
语文构成论的研究方法则与之相反,它是一种筹划性思维,它需要的是归纳、总结。它首先要确定的是语文课要达到什么目标,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开展哪些活动,开展这些活动要涉及到哪些“材料”,从这些活动和“材料”中,就总结出语文教育的成分和要素。
总之,语文本体与语文构成是两个不同的范畴,A+B这种回答方式误将一个构成论的回答当作本体论的回答。这是语文本体论与构成论的双重迷失。它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误导了语文教育。
一般来说,人们认为语文构成是由对语文本体的认识决定的,语文是什么的答案决定语文由什么构成,前者是后者的标准,是后者的分析工具。这种看法从逻辑上来讲是正确的。但是,认知思维与筹划思维并不是一种单一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认知思维与筹划思维在人类的思维发展上也并不是一种单一的先后关系。从思维发展历史的角度来讲,认知思维与筹划思维常常是互为前提、相互转化的,在很多情况下,常常是成熟的筹划思维催生了认知思维的发展,认知思维建立在筹划思维的系统化和理论化的基础上。当然,更多的情况下,是认知思维指导了筹划思维,人们根据自己对事实的理论认识,来筹划自己的实践活动目标、内容和方案。
应该说,目前关于语文的学术积累和理论准备,都不足以为我们提供语文是什么的答案。换句话说,关于语文的研究,还没有发展到由认知思维向筹划思维转化的“理性时代”。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片面强调从“语文是什么”到“语文教什么”曲本体论到构成论)的逻辑过程,可能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有的同志主张与其花那么多工夫讨论“语文是什么”这么一个抽象命题,不如回过头来看,我们的语文课到底应该教什么,这种主张,也许是对的,至少是有意义的。
2.语文是什么与语文不是什么
语文是什么,是语文本体论的正面设问,语文不是什么,则是语文本体论的反面设问。
在这篇小文章里,笔者想立足于语文教学实际,先从反面探讨一下,语文不是什么。然后再具体讨论一下语文的构成。
第一,语文不是语文的内容。语文和语文的内容的关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话题。应该说,这是一个老话题了。传统的观点是一个很简单但很有力的论证:文以载道,所以:文即道。现代,人们更是从内容与形式的哲学命题出发加以论证,证明二者之间内容的优先地位:内容是皮,形式是毛,皮之不存,毛将附焉?这里涉及到许多理论问题。比如:文与道是一个“载”的关系吗?即算回答是肯定的,由此可以得出文与道即是同一关系的结论吗?还比如:语文与语文的内容,是语文形式与语文内容的关系吗?语文的形式指的是什么呢?对于语文来说,语文的内容具有优先地位吗?内容只有在什么情况下才具有优先地位呢?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探讨的,都是不能简单地下结论的。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展的这一次语文教育大讨论,主题之一即是对语文教育人文内涵的失落提出了批判。作为一种纠偏,语文教学出现了一种称之为“人文教育”的倾向。在语文教材和语文课堂教学中,我们经常看见这样的设问:这篇课文表达了一个什么样的意思;认真阅读课文,请说出这篇文章的主旨。一些新编的语文教材,更是设计了大量的人文主题活动,围绕自然、社会、科学、艺术等话题,要生走入社会,走人大自然,了解社会,感悟人生,体验自然,贴近艺术。虽然在这些活动设计中,也有一些是要求学生查阅文字资料,有的最后也要求写出调查报告或者日头演讲的,但活动设计的主旨,它的目标指向,不在这些“语文活动”本身,而在了解社会、感悟人生、体验自然、贴近艺术这些人文主题。有人称这种貌似与语文有关、但其主旨却在语文之外的语文教学为“泛语文”。
一个最有力的质问是:这些教学活动与政治课、历史课、地理课、艺术课的教学有什么区别。如果说这些够活动设计因为涉及到了语文的运用很阅读资料、撰写报告、口头演讲等赋算是语文课的话,那么政治历史地理甚至物理化学课里不也有语文的运用甚至语文活动吗?
这种泛语文倾向实际上影响到了所有的语文教学,因为我们学的每一篇课文,都有一个人文的主题,《松鼠》不是一个自然的主题吗?《胡同文化》不是一个文化历史的主题吗?如果我们把这个自然的主题、文化的主题也都归于语文的教学内容的话,那么它与生物课、历史课有什么区别呢?
那么,什么是语文课与其他课程的区别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就是“语文是什么”的本体论答案。我们目前能说的是:语文课与其他课程是不一样的,因为语文与语文的内容不是一回事。张楚廷教授的这段论述也许可以给我们以启发:“当学习语言学的时候,并不特指某种对象,不是就某一类具体的事物来学习的,……也许都涉及到,但都不是特定对象;与其说它因涉及而负载了这一切,不如说一切涉及它自己一语言;也许通过学习它而涉猎了许多,但主要还是涉猎它自己一语言;它不拘束地回到自己。”语文教学的关键,是怎样从“某一类具体的事物”“回到自己”。这种“泛语文”的语文教学,则是迷失了自己。这无疑是一种本体论迷失。
第二,语文也不是一个知识系统。我们可以把数学当作一个知识系统来学,可以把历史当作一个知识系统来学,大致上是没错的。但我们可以把语文当作一个知识系统来学吗?
过去,我们主要是在“能力与知识”的范畴内来讨论语文与知识的关系的,这种视角很容易得出一些“知识是能力的基础”这种“很正确”的结论。现代学校教育是建立在“学校知识”的基础之上的,“知识化”“知识中心”是现代学校教育一种前提性、普遍性的'倾向。语文是现代学校教育课程体系中的一环,于是现代课程的设计者毫不犹豫地断定了语文的知识性质。
语文与知识的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语文的教学性质这个角度来考虑,正如王荣生博士所说,语文知识是用以描述语文教学的目标,借以指导教师理解语文教学、设计语文教学的不可或缺的工具。附语文本身来考虑,语文至少与程序性知识、策略性知识有关。这些知识,大致上收归在语用学这门学科里。在语文教学中,我们教一些这样的语文知识是有益的,必要的。
但是,从语文的本质这个层面来看,语文是超知识的,或者说是非知识的。语文更多地以直觉的形式呈现,语文更多地以知情意统一的特点引起人们的注意。现代哲学、现代语言学理论和心理学研究已经证明对语言的知识化理解是对语言的误解。过去,我们主要是在工具论的指导下断定语文的知识性质的,所谓工具论,其实就是语文知识论。实际上,工具论作为一种语言学理论,早已被现代哲学深深质疑。从马克思的“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到胡塞尔“语言是使认识成为可能的先验性条件”,从海德格尔“语言是存在的住所”到伽达默尔“语言是人类拥有世界的唯一方式”,从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到分析哲学的语言本体论从接受理论到语言建构主义,从认知语言学到语言人类学,它们都指向一个结论:语言远非工具,语言远非一个知识系统。
如果我们把语文看作一个学校教学的科目,则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即我们为什么要学语文知识。我们学物理知识的目的是为了掌握物理世界,我们学历史知识的目的是为了掌握历史;物理知识与历史知识都是“真理性知识”,它反映的是客观世界的必然规律,对这种客观必然规律的掌握是“掌握”物理与历史的必要条件。语文课程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一种可以称之为“语文智慧”(大家更能接受的表述是“语文素养”)的东西,语文知识对语文智慧的获得来说是不是不可或缺的呢?目前的研究似乎还不能证明这一点。语文知识是一种“非真理性知识”,它是建构的(传统的说法是“约定俗成”的);对于语文实践来说,重要的是获得这种建构的智慧,“约定俗成”的智慧。而有关研究表明,语文知识既不是建构语文、“约成”语文的充分条件,甚至也不是必要条件,而只是辅助条件。
总之,语文涉及到知识,但语文不能被看作一个知识系统,尤其不能当作一个知识系统来学。把语文当作知识来学,既不符合语文的规律,也不符合语文教学的规律。
3.教什么与什么是可教的
现在我们回到语文构成的论题上。它要解决的问题是:语文课教什么?
首先,这是一个实践设计的问题,它当然与语文本体有关,它必须符合语文本身的要求。但在整体上,它直接面向的,是语文教育的实际需要。换一句话说,教什么的问题,是把语文当作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来设计的问题,它除了涉及语文本身以外,还涉及到语文以外的其他要素,比方说与其他课程的关系,作为教育科目,它还必须体现国家意志或某一社会意识,等等。语文课教什么的设计,就是综合考虑这些因素的一种整体选择。我在这里强调“教什么”的可选择性、设计性,目的除了说明语文本体与语文构成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更重要的,是强调这种选择的相对性、阶段性、可变性:它是建立在目前大家对语文本体和与语文有关的其他社会因素的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它没有终极性,它随着人们对语文本体的认识的变化和社会实际需要的变化而变化,它是一种面向实际的实践选择,而不是理论的逻辑的证明,虽然它并不排斥理论的逻辑的证明。
当我们从“教什么”这样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时候,我们同样面临一个复杂的局面。就目前的研究来说,我们可以分析出语言、文章、文学和文化这么四个成分。几乎所有的研究最后都是从反面来论证的:语文能不包括语言吗,语文能不学文章吗,语文没有文学还是语文吗,语文能去除文化的含义吗。这种反面论证方法一方面说明它的这种研究不是穷尽的,也许在这四种成分以外还应有其他成分,另一方面说明,这种反面证明其不可或缺并没有解决它们在语文中到底占据一个什么位置的问题,它只是说明它们对语文来说不可或缺,但它们相互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它们各自对语文来说起着一个什么作用、被摆在一个什么具体的位置呢,这个问题对语文实践来说也许比判定它们是语文的一个成分或要素更重要。
那么,在语文中,语言、文章、文学与文化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当我们面临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有三个,第一,它们是一个层面的东西吗,第二,作为“教什么”的问题的一个回答,它们具有可教性吗,第三,也是更重要的,是什么东西把它们贯穿起来呢,统领它们的核心的东西是什么。
可以肯定地说,语言、文章、文学与文化这几个概念不是并列的,内涵上也在不同的领域。文章和文学是成文作品,文章与文学的区别在这种成文作品所在的不同领域与不同表现形式。文化是文章和文学的内涵,任何一篇成文作品,不管是文章还是文学,都是某一时代、某一类人的精神生活和实践生活的产物,都是某种“文化体系”的产物。直接地说,在文化学层面上,文章和文学都是人的精神生活和实践生活的成文表现形式,都是文化的物化形态(之一)。
那么语言在一个什么位置上呢?要论述清楚这个问题可能需要相当的篇幅,因为它涉及到一个广阔的学术背景。我们在这里直接引 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论述来说明这个问题。列维·斯特劳斯曾对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作过这样的归纳: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讲,语言是文化的一个结果;从哲学的角度来讲,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部分;而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讲,语言则是文化的一种条件。“首先,这是从历时性方面来看文化的条件,因为我们学习我们自己的文化大多是通过语言”;“另外,从理论性更强得多的观点来看,语言之所以可以说是文化的条件,是因为语言所赖以建立的材料同文化所赖以建立的材料是属于同一类型的:逻辑关系、对位、相关性,等等。由此观点来看,语言好像是为那些相应于与文化的不同方面的更复杂的结构奠定了一种基础”。斯特劳斯的意思是说,语言是比文化更基础的东西。人类文化活动和文化成果,就是建立在语言的基础之上的,是由语言提供基本成分和结构的。
事实上,如果我们把语言看作是一种工具,则很自然把它放置在第二个层面,而如果我们把语言看作是一种“世界观”,则很自然把它放置在第三个层面上。
以上论述使我们获得了一个语文要素的层次结构,第一层:文章与文学;第二层:文化;第三层:语言。那么,站在语文的立场上,我们怎么样将它们统一起来呢?我寻找到的概念是:言语。
不管是文章和文学,还是文化,还是语言,它们都被包容在“言语”的概念中,或者说,它们都能被“言语”这个概念所解释。文章和文学作为言语作品这是不证自明的,它们是言语作品的不同类型。从言语学的角度来看,文化正是对言语活动作为人的一种生活方式的哲学说明,换一句话来说,我们从哲学意义上来理解言语,言语就正是一种文化活动。至于语言与言语的关系,则早有前人的经典论述:“语言和言语活动不能混为一谈;它只是言语活动的一个确定的部分,而且当然是一个主要的部分。它既是言语机能的社会产物,又是社会集团为了使个人有可能行使这机能所采用的一整套必不可少的规约。”
文章与文学、文化、语言,都是语文的构成要素。我们把它们统一在“言语”的概念下:那么,我们在语文教学中,是不是把这四个要素都要作为语文教学的内容呢?一也是也不是。说“不是”,是因为教学内容是一个实体性的所指,在语文这个范畴内,文化的实体性所指不是别的,正是文章与文学。离开了文章和文学,(在语文这个范畴内)文化只是一个“概念”或“内涵”,作为一种概念性、内涵性的东西,它只能让人领悟到,思索到,体验到,却无法使它在教学活动中与学生“接触”,因而没有可教性。语言是可教的,但可教的语言是物质形态的语言,是知识形态的语言,而“世界观”形态的语言则是不可教的,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作为文化的条件的语言是不可教的,因为它是一种“背景性”的存在。说“是”,是因为文章和文学、文化、语言四个范畴是相互层叠蕴涵的,它们是全息性的四个范畴。“语言结构是‘许多系统的系统’,或者说各种相互有关的范畴的‘网络’,其中没有哪个部分是完全独立的,或者完全从属于另一部分的。就语言来说,在把一切都学会以前,没有哪一部分可以完全学会的。”皮特·科德的这段论述,对语文这四个要素都是适用的。
于是我们获得关于语文的一种结构描述:以文章和文学为语文的基本要件;以文化为内在的意蕴与价值取向;以语言为基础;以言语观为基本立场(一个理解语文的理论视域)。由此我们获得了语文教学的几条基本原则:从言语的角度来理解语文、把握语文;从语言的这个基本层面走向语文;着眼于文化的意蕴展开语文教学;着力于文章和文学这两个方面来实施语文教学。其基本要义可以概括为:明确文章教育与文学教育两个阵地;都要从文化来立意;都以语言为基础;都作为言语来学。
注释:
①张楚廷:课程与教学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59.
②参见王荣生:语文科课程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259-268.
③参见拙著:言语教学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254-265.
④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72.
⑤[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30.
⑥[英]皮特·科德:应用语言学导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3,3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