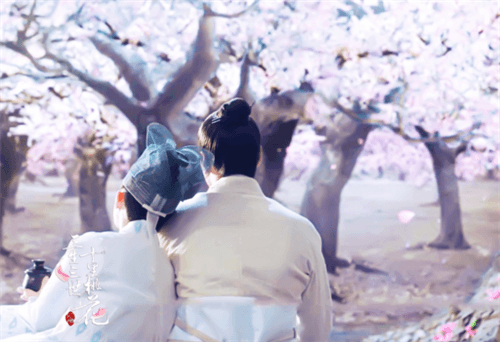
创作短篇小说作文600字【一】
小羊虽然吓得发抖,但是他很聪明。小羊说:
“狼伯伯,求求你,在吃掉我以前,能否吹个笛子给我听呢?”
“什么?吹笛子做什么呢?”
“我想在死之前,配合着笛声,跳一下我最喜欢的舞。”
“该不会打算边跳舞边溜走吧!”
“不会、不会,我绝不会逃走!”
“好吧!我就吹一曲吧!”
狼吹起笛子,小羊配着调子跳舞,跳得很可爱。
牧羊人听到笛声,跑了过来。
“啊!是狼!”
牧羊人愤怒的将狼抓住,救了小羊。
狼非常的懊悔。
“上当啦!那是小羊向牧羊人求救的信号啊!”
创作短篇小说作文600字【二】
从前有只狐狸向狼谈起人的力量,说没有动物能抵挡得了,所以他认为所有动物都必须施展计谋才能保护自己。可狼回答说:“假如我有机会碰到一个人,我就扑上去让他无法抵挡。”
狐狸说:“我可以帮你碰到人啊。明早你早点来我家,我把他指给你看。”
第二天,狼很早就来了,狐狸带它来到猎人每天的必经之路。
他们碰到的第一个人是个退役老兵,狼问:“那是个人吗?”
“不是,”狐狸回答,“他以前是。”
接着他们遇到一个去上学的小男孩。
“那是个人吗?”狼又问。
“不是,”狐狸回答说,“他将来是。”
最后一个猎人朝它们走来,他肩上扛着双筒猎枪,腰间还插着一把猎刀,狐狸对狼说:“那个就是人,你该朝他扑过去,我可是要回我洞里去了。”
于是狼朝猎人冲了过去。猎人一看说:“真可惜我没装上子弹,而是散弹。”
他瞄准狼的脸开了一枪。
狼疼得一阵痉挛,可还是没被吓倒,又朝猎人冲了过去。猎人又开了一枪。
狼忍着巨痛扑向猎人,没想到猎人抽出猎刀左右开弓地在狼身上划了几道口子。狼鲜血四溅,嚎叫着逃到狐狸那里去了。
“狼兄弟,” 狐狸说,“和人相处怎么样?”
“哈!”狼回答说,“我从没想到人的力量会这么大!他先是从肩上取下一根棍子,朝里面吹了一口气,就有什么东西飞到我脸上,痒得我要命;接着他又吹了一次,就有东西飞到我鼻子周围,像下了一阵雹子。当我靠近他时,他从身上抽出一根白得发亮的肋骨狠狠地打我,几乎把我打死在那里。”
狐狸说:“你这个吹牛大王,谁让你把话说得太大了,自己连退路都没有了呢。”
创作短篇小说作文600字【三】
既然小说都存在着读者,那么小说就一定存在着读者看小说时的感受。试问:如果读者读某部小说的或人物或情节或环境甚至细节时的感受是——这是虚构的,不是真实的。那么,读者还会继续读下去么?我想,没有读者愿意去读一部自己感觉不真实的小说。没有人愿意去读某部小说,就意味着这部小说没有读者,而没有读者的小说是绝对不能称之为小说的。
也就是说,一部成功的小说,一定是能让读者读出“真实”的小说,纵然这种“真实”明明是“虚构”的。我国古典小说《西游记》、《聊斋志异》情节是何等离奇,妖魔鬼怪各逞凶顽,飞禽走兽尽显神通,讲的是神怪,但是我们并不感到荒诞,相反受到感染得到启迪进而百读不厌。这些作品千百年来久传不衰,究其原因,固然很多,但根本原因还在于它们都让读者读出了真实。
怎样才能让读者从小说中读出真实,这是作者写小说时应该注重并落实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要让读者读出真实,作者必须写出真实,这就好比你手中必须有馒头,才能给乞丐馒头吃。否则你把一双空手伸给乞丐,对他说:给!馒头!那你一定是在骗人。乞丐不会接受你的“空手馒头”,读者更会拒绝你的失真文字。
怎样才能写出真实?窃以为作者必须本着一颗真心去写作。所谓真心,其实就是对小说中每个人物每个情节每个环境都倾注都寄予真情实感。美国作家利昂·塞米利安说:“在一个真正作家的气质中,总有一种近于痴狂的激情”,而这种“近于痴狂的激情”无疑是“真心”“真情实感”最好的诠释与体现。早先曾听许多人说写小说的都是疯子,起初很是反感,认为是对自己的污蔑与诽谤。但后来却无数次地在深夜为笔下的人物为笔下的情节大哭特哭,伤心欲绝感动欲绝悲愤欲绝,到那时我才终于知道自己的真心已经融入笔下的人物,痛着他们的痛、乐着他们的乐,甚至为他们神思恍惚、物我两忘。说到底,不也是进入了一种痴狂的境界,难以自拔么?当然,也正因为小说的字里行间倾注了我全部的真心真情、浸透了我太多的心血泪水,读者在读的过程中才会觉得真实感人,才会热泪奔涌秉烛夜读。
从小说创作而言,作者的确需要有一种“近于痴狂的激情”,但这种激情又必须有所节制,切忌让那种“痴狂的激情”完全左右了作者的头脑,那就近乎危险了。正如美国作家利昂·塞米利安说:“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不受节制的激情只是激情而已,而有所节制的激情则是天才。”所以作者写小说时千万不要“走火入魔”,否则写完主人公跳楼自己就会爬到楼顶,那么痴情的读者读小说时也会“走火入魔”,会因为主人公的跳楼而跳楼。
写出真实,不能等同于照录生活。在日常写作与阅读中,我们也常常有这样的体验:有时,一些记述真实生活的文字,读起来反而味同嚼蜡,有隔膜之感、虚假之感。这就是小说与生活的区别,有些事在生活中毫无疑问是真实的,而一旦被写成文字,冠名于小说,就毫无疑问是虚假的。因为小说是艺术,小说虽然取材于生活,但一定要高于生活。而这个“高于生活”,便是我们耳熟目悉的艺术加工——虚构。
写小说就得虚构,如果不虚构,那就正如作家张天翼先生指出的:“一个作家要是只限于写真人真事,那就是自己束缚自己了。”这是从作者的角度来说,如果从读者的角度去说,当我们读《西游记》《聊斋志异》时,明明知道它们全是虚构的,却在心底依然被其感染感动,或者我们一直不曾有半分怀疑的人和事甚至一直感动着的情景、状态、细节,却突然在某一天因被作者亲口证实是他虚构的而义愤填膺等等,这就是艺术真实的魔力或曰魅力。
对生活进行艺术的加工,这便是小说的创作。在真实的基础上进行虚构,在虚构中倾注真心真情,这便是小说创作之核心。实者虚也,虚者实也,虚虚实实如能恰倒好处,纵然假,也足以以假乱真,无人质疑。
创作短篇小说作文600字【四】
??短科幻小说续写地球上最后一个人独自坐在房间里,这时,忽然响起了敲门声……
他蹑手蹑脚的走到门旁,屏住呼吸,手缓慢地掀开猫眼,把脸侧贴到门上,左眼紧闭,右眼睁大,眼球死盯着门外,找了几秒,却什么都没有发现,仍旧是一样的景色。他提起的心这下次可落了下来。他拍着胸膛,在心中默念:刚刚一定是神经太紧张,造成了幻听。他刚要走开,突然,“咚咚~~~”那敲门声再次响起,他刚刚落下来的心又再次提起,没等他反应过来,又一次敲门声响起,比上次更加有力,大声。他心想:不管外面是魔鬼是神还是其它什么东西,只能硬着头皮上了!他来到门边,再次掀开猫眼,观察,却仍旧空无一物。他视线往下一移,心底一惊:
那是一个满身穿戴着盔甲的不明生物。那不明生物明明只有五岁儿童般身高,却老态龙钟,相貌与人类相差不远,酒槽鼻,厚嘴唇,眼神如同鹰般锐利,橙色略带银丝的头发和胡子连在一起,身上的铁质盔甲带有一丝丝裂痕,盔甲没有掩盖的手臂上,那应肌肉发达而造成的青筋暴起,右手上提着一个印有狮子头像的锤子,眼镜四处张望,头却不偏离前方,左手不住的敲着门,每一次都比一次用力。他想:这是什么生物?矮人?矮人不是只在传说中存在吗!怎么可能是真的.?不可能!不可能!
就在这时,门外的“矮人”仿佛不耐烦了,提起手中的重锤,两手握住,朝着铁门就是一锤,那怪力硬生生地将铁门凹进去一个大坑,他在门外吓得瘫倒在地上,心中不断念叨着:哪个天仙佛祖上帝耶稣不管是谁都救救我吧!而门外的“矮人”仿佛没垂倒门而发怒,“矮人”将锤子放到地上,震起了一片尘土,其重量可想而知!“矮人”甩甩双手,将锤子提起,又是猛地一发力,里面的人才刚有勇气爬起来逃离,那连门带墙都倒塌下去,带起了一阵尘土,蒙蔽了“矮人”和地球上最后一个人的双目。带尘土过去后,地球上最后一人还在震撼这个怪力,然而“矮人”却马上反应过来,脚上一发力,那势头仿佛猛虎下山般,一下子冲到地球上最后一人面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锤锤死了地球上最后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