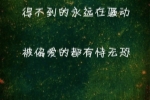《满分作文》这本书作者是谁【一】
我只说您永远也收不到我的那封信了,可怎么也没有想到您的信竟能邮来,就在您死后的第十一天里。今天的早晨,天格外冷,但太阳很红,我从医院看了病返回机关,同事们就叫着我叫喊:"三毛来信啦!三毛给你来信啦!"这是一批您的崇拜者,自您死后,他们一直浸沉于痛惜之中,这样的话我全然以为是一种幻想。但禁不住还在问:"是真的吗,你们怎么知道?"他们就告诉说俊芳十点钟收到的(俊芳是我的妻子,我们同在市文联工作,她一看到信来自台湾,地址最后署一个"陈"字,立即知道这是您的信就拆开了,她想看又不敢看,啊地叫了一下,眼泪先流下来了,大家全都双手抖动着读完了信,就让俊芳赶快去街上复印,以免将原件弄脏弄坏了。听了这话我就往俊芳的办公室跑,俊芳从街上还没有回来,我只急得在门口打转。十多分钟后她回来了,眼睛红红的,脸色铁青,一见我便哽咽起来:"她是收到您的信了……"
收到了,是收到了,三毛,您总算在临死之前接收了一个热爱着您的忠实读者的问候!可是,当我亲手捧着了您的信,我脑子里刹那间一片空白呀!清醒了过来,我感觉到是您来了,您就站在我的面前,您就充满在所有的空气里。
这信是您一月一日夜里两点写的,您说您"后天将住院开刀去了",据报上登载,您是三日入院的,那么您是以一九九○年最后的晚上算起的,四日的凌晨两点您就去世了。这封信您是什么时候发出的呢,是一九九一年的一月一日白天休息起来后,还是在三日的去医院的路上?这是您给我的第一封信,也是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更是您四十八年里最后的一次笔墨,您竟在临死的时候没有忘记给我回信,您一定是要惦念着这封信的,那亡魂会护送着这封信到西安来了吧!
前几天,我流着泪水写了《哭三毛》一文,后悔着我给您的信太迟,没能收到,我们只能是有一份在朦胧中结识的缘分。写好后停也没停就跑邮局,我把它寄给了上海的《文汇报》,因为我认识《文汇报》的肖宜先生,害怕投递别的报纸因不认识编辑而误了见报时间,不能及时将我对您的痛惜、思念和一份深深的挚爱献给您。可是昨日收到《文汇报》另一位朋友的谈及别的内容的信件,竟发现我寄肖宜先生的信址写错了,《文汇报》的新址是虎丘路,我写的是原址圆明园路。我好恨我自己呀,以为那悼文肖先生是收不到了,就是收到,也不知要转多少地方费多少天日,今日正考虑怎么个补救法,您的信竟来了,您并不是没有收到我的信,您是在收到了我的信后当晚就写回信来了!
读着您的信,我的心在痉挛着,一月一日那是怎样的长夜啊,万家灯火的台北,下着雨,您孤独地在您的房间,吃着止痛片给我写信,写那么长的信,我禁不住就又哭了。您是世界上最具真情的人,在您这封绝笔信里,一如您的那些要长存于世的作品一样至情至诚,令我揪心裂肠的感动。您虽然在谈着文学,谈着对我的作品的感觉,可我哪里敢受用了您的赞誉呢,我只能感激着您的理解,只能更以您的理解而来激励我今后的创作。一遍又一遍读着您的来信,在那字里行间,在那字面背后,我是读懂了您的心态,您的人格,您的文学的追求和您的精神的大境界,是的,您是孤独的,一个真正天才的孤独啊!
现在,人们到处都在说着您,书店里您的书被抢购着,热爱着你的读者在以各种方式悼念您,哀思您,为您的死作着种种推测。可我在您的信里,看不到您在入院时有什么自***的迹象,您说您"这一年来,内心积压着一种苦闷,它不来自我个人生活,而是因为认识了您的书本",又说您住院是害了"不大好的病"。但是,您知道自己害了"不大好的病",又能去医院动手术,可见您并没有对病产生绝望,倒自信四五个月就能恢复过来,详细地给了我的通讯地址和电话号码,且说明五个月后来西安,一切都作了具体的安排,为什么偏偏在入院的当天夜里,敢就是四日的三点就死了呢?!三毛,我不明白,我到底是不明白啊!您的死,您是不情愿的,那么,是什么原因而死的呀,是如同写信时一样的疼痛在折磨您吗?是一时的感情所致吗?如果说这一切仅是一种孤独苦闷的精神基础上的刺激点,如果您的孤独苦闷在某种方面像您说的是"因为认识了您的书本",三毛,我完全理解作为一个天才的无法摆脱的孤独,可牵涉到我,我又该怎么对您说呢,我的那些书本能使您感动是您对我的偏爱而令我终生难忘,却更使我今生今世要怀上一份对您深深的内疚之痛啊!
《满分作文》这本书作者是谁【二】
??本书真好看-500字晚上七点,家家香气弥漫,当然东东家也不例外。从厨房里传来一阵叮叮咚咚的`声音,原来是妈妈这位大厨正在做着晚饭,身为球迷的爸爸也抱着电视机看着球赛,不时的欢呼着:“太好了!进了!”,而一向成绩很好的东东,却不知在卧室干着什么。“开饭喽”随着妈妈温柔的呼叫,爸爸就像个小磁石一样,被吸铁般的饭桌吸了过去,爸爸刚要拿起筷子夹一块又红又肥的红烧肉,就被妈妈制止了:“没看见儿子缺席了吗。赶快叫他去。”爸爸无奈,只好去卧室找东东。
“东东,快来吃饭,有你最爱吃的红烧肉!”爸爸大声叫道,可是没有回音,爸爸的脚步加快了,决定去一探究竟,爸爸推开了卧室门,看到儿子正在津津有味得看着一本书,爸爸推着儿子说:“吃饭了,”儿子这才记起该吃饭,便走向客厅,爸爸瞟了一下了书……
东东坐到了座位上,妈妈问:“你爸呢?”东东摇摇头,跑向卧室,爸爸正在目不转睛地看着那本书,儿子说:“爸爸,我不看,怎么你又看起来了,”爸爸笑着,不好意思地走向客厅。
东东边吃边想:这本书可真好看,爸爸差点就被他迷住了。
《满分作文》这本书作者是谁【三】
——莎士比亚
也许是厌倦了苦燥无味的化学方程式,也许是为了逃避令人窒息的x+y,我切盼着每天与你见面。你一次又一次地陪伴着我,你用那泛着清香的扉页,引领着我走向一个鲜活的世界——我心中那份渴望、那片怡人的“绿地”。
你的知识广阔无垠,你的语言富有哲理。你的目光是那么温暖,好像能融化世界上所有冰冻了的心,你的双手是那么温柔,好像能抚平人间的累累伤痕……
当我因失败而痛苦迷惘时,你总这样对我说:“真正的光明并不是没有黑暗的时候,只不过永远不为黑暗所遮蔽罢了;真正的英雄并不是永远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不为卑下的情操所左右罢了;当你要战胜外来敌人时,首先得战胜你内在的\'敌人,你不必害怕沉沦堕落,只要你不断地自拔与更新。”
当我因成功而手舞足蹈时,你总这样对我说:“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强中更有强中手。真正的强者,不但要经得起失败的考验,还要经得起成功后糖衣炮弹的洗礼,当你沉浸在幸福的甜蜜里赏花赏月时,只怕别人已到了峰巅了。”
当我因困惑而不能自拔时,你总这样对我说:“人的一生中会遇到很多人,有的是流星,有的是恒星。流星是美的,可它终究是一颗流星,流星的意义在于瞬间即逝,流星的美也只源于刹那间。流星毕竟是流星,若追寻长久,只能等待属于自己的那颗恒星,死死地抓住这瞬间的美,痛苦只能是自己。”
当我畏首畏尾踌躇不前时,你给我送来这样的诗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是啊!这就是你,不管是树荫之外喧嚣着浮躁的热浪,还是窗外肆虐着凛冽的寒风,只要和你在一起,就会在热浪之中享受一片清凉,在严寒之中享受一份温暖……
《满分作文》这本书作者是谁【四】
一晃荡,我在城里已经住罢了二十年,但还未写出过一部关于城的小说。越是有一种内疚,越是不敢贸然下笔,甚至连商州的小说也懒得作了。依我在四十岁的觉悟,如果文章是千古的事--文章并不是谁要怎么写就可以怎么写的--它是一段故事,属天地早有了的,只是有没有宿命可得到。姑且不以国外的事作例子,中国的《西厢记》、《红楼梦》,读它的时候,哪里会觉它是作家的杜撰呢?恍惚如所经历,如在梦境。好的文章,囫囵囵是一脉山,山不需要雕琢,也不需要机巧地在这儿让长一株白桦,那儿又该栽一棵兰草的。这种觉悟使我陷于了尴尬,我看不起了我以前的作品,也失却了对世上很多作品的敬畏,虽然清清楚楚这样的文章究竟还是人用笔写出来的,但为什么天下有了这样的文章而我却不能呢?!起来,往日企羡的什么词章灿烂,情趣盎然,风格独特,其实正是阻碍着天才的发展。鬼魅狰狞,上帝无言。奇才是冬雪夏雷,大才是四季转换。我已是四十岁的人,到了一日不刮脸就面目全非的年纪,不能说头脑不成熟,笔下不流畅,即使一块石头,石头也要生出一层苦衣的,而舍去了一般人能享受的升官发财、吃喝嫖赌,那么搔秃了头发,淘虚了身子,仍没美文出来,是我真个没有宿命吗?
我为我深感悲哀。这悲哀又无人与我论说。所以,出门在外,总有人知道了我是某某后要说许多恭维话,我脸烧如炭;当去书店,一发现那儿有我的书,就赶忙走开。我愈是这样,别人还以为我在谦逊。我谦逊什么呢?我实实在在地觉得我是浪了个虚名,而这虚名又使我苦楚难言。
有这种思想,作为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人来说,我知道是不祥的兆头。事实也真如此。这些年里,灾难接踵而来,先是我患乙肝不愈,度过了变相牢狱的一年多医院生活,注射的针眼集中起来,又可以说经受了万箭穿身;吃过大包小包的中药草,这些草足能喂大一头牛的。再是母亲染病动手术;再是父亲得癌症又亡故;再是一场官司没完没了地纠缠我;再是为了他人而卷入单位的是是非非中受尽屈辱,直至又陷入到另一种更可怕的困境里,流言蜚语铺天盖地而来……。我没有儿子,父亲死后,我曾说过我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现在,该走的未走,不该走的都走了,几十年奋斗的营造的一切稀里哗啦都打碎了,只剩下了肉体上精神上都有着毒病的我和我的三个字的姓名,而名字又常常被别人叫着写着用着骂着。
这个时候开始写这本书了。 要在这本书里写这个城了,这个城里却已没有了供我写这本书的一张桌子。 在一九九二年最热的天气里,托朋友安黎的关系,我逃离到了耀县。耀县是药王孙思邈的故乡,我兴奋的是在药王山上的药王洞里看到一个"坐虎针龙"的彩塑,彩塑的原意是讲药王当年曾经骑着虎为一条病龙治好了病的。我便认为我的病要好了,因为我是属龙相。后来我同另一位搞戏剧的老景被安排到一座水库管理站住,这是很吉祥的一个地方。不要说我是水命,水又历来与文学有关,且那条沟叫锦阳川就很灿烂辉煌;水库地名又是叫桃曲坡,曲有文的含义,我写的又多是女人之事,这桃便更好了。在那里,远离村庄,少鸡没狗,绿树成荫,繁花遍地,十数名管理人员待我又敬而远之,实在是难得的.清静处。整整一个月里,没有广播可听,没有报纸可看,没有麻将,没有扑克。每日早晨起来去树林里掏一股黄亮亮的小便了,透着树干看远处的库面上晨雾蒸腾,直到波光粼粼了一片银的铜的,然后回来洗漱,去伙房里提开水,敲着碗筷去吃饭。夏天的苍蝇极多。饭一盛在碗里,苍蝇也站在了碗沿上,后来听说这是一种饭苍蝇,从此也不在乎了。吃过第一顿饭,我们就各在各的房间里写作,规定了谁也不能打扰谁的,于是一直到下午四点,除了大小便,再不出门。
我写起来喜欢关门关窗,窗帘也要拉得严严实实,如果是一个地下的洞穴那就更好。烟是一根接一根地抽,每当老景在外边喊吃饭了,推开门直感烟雾笼罩了你了!再吃过了第二顿饭,这一天里是该轻松轻松了,就趿个拖鞋去库区里游泳。六点钟的太阳还毒着,远近并没有人,虽然勇敢着脱光了衣服,却只会狗刨式,只能在浅水里手脚乱打,打得腥臭的淤泥上来。岸上的蒿草丛里嘎嘎地有嘲笑声,原来早有人在那里窥视。他们说,水库十多年来,每年要淹死三个人的,今年只死过一个,还有两个指标的。我们就毛骨悚然,忙爬出水来穿了裤头就走。再不敢去耍水,饭后的时光就拿了长长的竹竿去打崖畔儿上的酸枣。当第一颗酸枣红起来,我们就把它打下来了,红红的酸枣是我们惟一能吃到的水果。后来很奢侈,竟能贮存很多,专等待山梁背后的一个女孩子来了吃。这女孩子是安黎的同学,人漂亮,性格也开朗,她受安黎之托常来看望我们,送笔呀纸呀药片呀
《满分作文》这本书作者是谁【五】
回到上海,与阔别十余年的她见面,她依旧梳着羊角辫,一副天真可爱的模样。如果不是我知道,很难把她和世界五百强企业的HR联系到一起。十年的打拼里,她的每一个老板,都夸她能慧眼识人。
“你是怎样在一堆又一堆的烂贝壳里,发现一粒又一粒珍珠的?”看她一脸的.不谙世事,我不禁有些疑惑地问。
她看着我一脸迷茫,笑了笑:“很简单啊,我知道他是谁,就像你要知道你是谁一样!”
原本就稀里糊涂的我,愈加迷糊了。
她端起还氤氲着香气的摩卡,轻抿一口,问我:“现在是什么季节啊?”
我愣了愣,看着窗外的艳阳天,懒懒地回答她“夏季”。
“哦,”她故作惊讶,又说,“你注意到他们的穿着没有?”
扫视四周,大都是T恤、衬衫、裙子……我说:“这不都是夏季标志性的穿着吗?有什么好奇怪的?这跟识人有什么关系?”
她并不回答我,“是啊,这些服饰一下子就能让你辨清季节,可以让你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穿,什么时候不能穿!”
“嗯。”我只好耐住性子。
“你再想想,是不是还有一些服饰,它们四季皆宜,没有明显的特点,只要你想,就可以穿戴。但你每次却穿得很纠结,是不是?”她睁大眼睛看我,很认真。
我想了想,还真是这回事,每次想着反正什么时候都能穿,还不如等下次,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等着下次。
“还有一些服饰呢,它可能会让你在一场晚会上出尽风头,让你在一场宴席中享受万千宠爱,可只要过很短很短的时日,它便再无用武之地,是吗?”
“是的”,我好像有点明白她想说什么。
她露出两个好看的酒窝,“其实呢,我用人也会把它们分成三类,一类呢,像华丽丽的晚礼服,拥有很多的荣耀,这也尝试过,那也尝试过,可没有一件事情能坚持做下去,没有特别地成功过。这类人大都华而不实,看起来很好,但很容易过期!”
“还有一类人呢,就如一件四季皆宜的衣服,过去是四平八稳,对未来也无欲无求,不犯什么过错,也没作出过特别的贡献。这类人你看不出他的好,也说不出他的不好,用在哪都让你安心,但也失了更好的希望!”她喝一口摩卡,顿了顿继续说。
“那还有一类呢?”
“还有一类,他们好似夏季的衬衫、冬天的羽绒服,棱角分明,他们的优点很特别,同样,他们的缺点也很突出,你能说出他的好,也可以指出他们的不足。用他们,你只需要扬长避短,往往就能带给你意想不到的收获!”她说完,长长地舒一口气。
与她作别的时候,我突然想明白了她的那句“你要知道你是谁”!
是的,行走世间,你是一尾草,你就努力地长叶;你是一朵花,你就努力地绽放;你是一棵树,你就努力地结果。你要知道你是谁,你只有知道你是谁,才会站在属于自己的地方,绽放出属于你的光芒,在职场上立于不败之地!
《满分作文》这本书作者是谁【六】
活着是需要勇气和智慧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我开始厌恶虚伪了,我崇拜真实,我爱看真实的东西,爱说真实的话,哪怕一些难以启齿的事情我也会毫不忌讳的讲出来,然而,仔细想来,却发现自己依然是虚伪的活着,活在虚伪里。正因为如此,我才找不到真实的自我了,所以,我会常常发自肺腑的问自己我是谁?
人活一世,有些人活的风风光光,有些人却猥猥琐琐,有些人潇潇洒洒,有些人却踉踉跄跄,作为不甘落后与平庸的人,我不能迷失在这个世界里,人活着总得拿出点儿活着的证据,而我一无所有,所以我得寻找那些活着的证据,我必须站在旁观者的立场审视自己,重塑自己。
我还很年轻,路还很漫长,有些目标没有达到,有些理想没有实现,前方总是新鲜的,如果趁现在努力,一切皆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