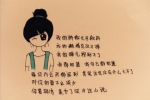作文有这样一种声音教学【一】
青青嫩草微微凹陷,一老一少坐在土堆之上。繁星点点,包围了那轮弯弯弦月,散发发着淡淡的白光,如同断丝的珍珠,散落在这玄色的天空之中。
静谧的夜时不时传出几声蝉叫,蛙鸣相夹着蝈蝈的细语。微风轻拂着夜的脸庞,如同情人一般絮语。几缕笛音箫声遁入夜空,带着长风破浪之势,却又有着几分杨柳般的轻柔,欢快的曲调让人眼前一亮。昆虫们更加雀跃的,细语却还是那般,生怕打扰了这悠悠之声。
远处的房屋发处淡淡的,黄色的微光,给这夜更带上了一抹神秘的面纱。微风拂过我的短短的黑色的发梢,带着泥土的气息,夹杂着这夜雨露的清香,还带着那远方鸟儿的\'鸣叫。我扎着一对牛角辫,一只手撑着大概只有半个巴掌大大的脸,两只小脚悬空着,晃来晃去,睁得大大的幽黑色的眼瞳望着那墨绿色有着八个孔,还挂着一个大红色平安结的东东,不禁问道:爷爷,这是什么啊?“萧。”那我可以玩玩吗?老人将它递入我的手中,急急的我立马学着将它放到口边,猛地吹了口气,不料却刮破了这夜的宁静……我不满地撸了撸嘴,爷爷却摸着我的头说:“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只有多次尝试才会成功的哦!没有人一学就会的。”
如今的我遇到过许多次失败,上的失利、对于难题的不懂还有种种,这些都让我心灰意冷,但当我每次想放弃时,耳畔总会响起那个声音——没有人一学就会。
作文有这样一种声音教学【二】
“嚓嚓嚓,咔咔咔”
我睁了睁朦胧的睡眼,又往被窝里缩了缩,蹬了蹬妈妈昨晚临睡前给我盖上的压脚被,伸手按了一下手机,五点钟,还早,但门缝里透过的隐约灯光和传来的微弱切菜声说明,妈妈已经在做饭了。我又往枕头上拱了拱,揉了揉眼睛,便穿上衣服起床了。
打开卧室门,推开隔断门,拉开厨房门,看到妈妈正站在灶台前,一手举着铲子,一手正在揭锅盖,案板上堆放着切好的蔬菜,锅中煮着的米粥传来“咕嘟咕嘟”的冒泡声,旁边的\'热油锅中爆着“噼啪噼啪”的响声……
我的突然出现,着实让母亲吓了一跳,问:“怎么起来了?是不是被做饭的声音吵醒了?我明明记得把门都关好了的……”
我不敢回答是,因为妈妈怕吵到我,已经做了很多准备:高压锅的喷气声很大,她就提前20分钟起床,用普通锅烧饭;抽油烟机动静太大,她就关上门,打开窗做饭,虽然油烟呛得她直咳嗽……
我笑了笑说:“没有,是我自己睡醒的。”
妈妈“哦”了一声,用手撩了一下前额落下的碎发,加快手中铲子翻动的频率。一股油烟扑面而来,呛得我快流眼泪了。
我赶紧背过身去,对妈妈说:“还是打开油烟机吧!”妈妈说:“不行,你和爸爸还没睡好,这声音太大了,我想让你们多睡会儿……”我忍不住问:“妈你就不怕呛吗?”“我是***妈嘛,没有什么的。”妈妈好象完全不在意的随口说到。
我的眼泪流了下来,不知是因为油烟抑或是什么其他,总之,是流下来了。
我似乎听到了妈妈心跳的声音,“咚咚、咚咚”,同那切菜声和水烧开的声音融为了一体。
这样的一种声音,怎会将我吵醒?我想,伴着这声音的睡眠,一定是甜蜜的,梦中也仿佛能听到你心跳的声音。
有那么一种声音,虽是噪音却让你感动;有那么一种爱,是真正的奉献,却不求回报;就如同有那么一个人曾用行动告诉你,她很爱你……
作文有这样一种声音教学【三】
那是一个周六的傍晚,我上完素描课,独自穿过家附近铁路下的一条隧道,来往的人车很多,环卫工人却很少来这里打扫。这时,我瞥见了一张被人随手丢弃的纸巾。它静静地躺在昏暗的隧道里,白的那么刺眼。我的注意力被它吸引了,脑中如激起千层浪一般,纠结开了。我要去把它捡起来吗?尽管周围的人车混杂声不绝于耳,但我却充耳不闻。我应该把它捡起来再扔到垃圾桶里去吗?可是万一上面沾满了病菌呢?我还是别管它了吧。可是别小看这张纸呀,如果人人都像你一样,白色污染迟早会毁了这个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的。但是我此刻背着沉重的包,拎着画箱,疲倦的身躯不容自己再实行那弯腰,捡起,再扔掉这一看似简单却劳累的`动作。我的心陷入了矛盾......结果就是:这么长时间的心理斗争仅仅浓缩成了那几秒:转过头去,再转回来,漠然地经过了那个思想碰撞的地带。没再回头,身后,却是昏暗隧道里,那刺眼的白色......
现在回想起这件事,我追悔莫及。我痛恨那时我的私心与惰性。如今,处处都能看见与那年不径相同的刺眼白色,每天的空气污染指数都逐步上升。成堆的生活垃圾渐渐吞噬着这个原来美丽的星球。在一霎那间,我感到自己是个罪人,甚至比那乱扔垃圾的人罪状更甚。现在很少有人能主动地去捡起垃圾,冷漠逐渐残蚀着人性,同时却又不敢抬头面对这片天空。
当电锯“咝咝”地响着,人们竟毫无节制砍伐森林时,你听见木桩的悲叹声了吗?当一阵枪响之后,猎人把飞翔的小鸟射落枝头时吗,你听见飞旋的羽毛的战栗声吗?当人们将枝头盛开的花朵拦腰折断时,你听见飘落花瓣的哭泣声了吗?当城市的发展渐渐吞没了绿色时,天不再蓝,水不再清,这时你才听见吗?
是的,我听见了。我走上前去,弯腰捡起了那团不再刺眼的白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