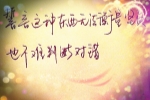英文作文通知类【一】
三月,丁香始盛开。
不求与百花争艳,但求在春风下嫣然一笑;没有流萤彩蝶作点缀,但求清风带走她的微香。
在百花丛中,他的色彩显得比原来更为黯淡,只有那一抹淡紫,向天空发出微弱的生命告示。可悲,可叹,天空一角留下一卷残云。
适逢遇上三月,江南一带缺不了雨水,油纸伞哼出来的小调,凄清,惆怅。古稀年的深巷,匿藏着颓垣的老屋,豆大的雨水从瓦尖滚然落下,与地上的积水融为一体,且不忘留下涟漪作记号。
凄婉,迷茫,紫丁香。
悠长的雨巷,颓圮的篱墙,一枝紫丁香从两砖间的罅隙伸展出来,留足注看,伞尖落下的水滴刺破了花蕾的静态,随即带动伏在花蕾上的水珠,簌簌落下,与布满青苔的石阶,迸溅出一朵朵小水花。
不禁伸手去触碰那带雨的花蕾,然而,望着那忧愁的淡紫,油然起了恻隐之心。
霏霏的细雨,随风飘洒,寂静的雨巷,如氤氲般凄婉,迷茫。空气中的雨雾迷糊了双眼,再望那支紫丁香,小小的花蕾里仿佛包容着世间上的一切忧怨,一切愁结。
惆怅,渐远渐近;巷外,万紫千红。
春雨,放缓了落地的脚步,直至湖畔的水一晕一晕地化为静态。雨终于停了,在紫丁香的哀愁中停了下来,初春亦不再随风徘徊,安稳地坐落在这哼着小调的江南。
思悠悠!巷外这枝紫丁香,在初春的时候,却忘了与巷外的众花齐放,独自在这悠长又寂寞的古巷,延续着雨的哀曲。
英文作文通知类【二】
我是扬州人,自是爱吃,这一年在外游历偏多,吃过各个地方的味道,五味可算得是一一尝遍。酸,都说山西人爱吃酸,隔着老远都能闻见醋味。以前在大学里,倒是有个山西的同学,不见吃了多少醋。说起醋,镇江的陈醋、香醋才是数一数二的。在杭州饭店里的醋大多不正宗,兑了水,蘸着饺子,没吃出多少醋味。有时候我食欲不振,需要些刺激性的食物开味,但是不能吃辣,常用的方法就是在扬州炒饭里倒上一两勺的镇江香醋,特下饭,一顿能吃好几碗。酸菜鱼算不上酸,麻辣味更重些,更何况现在街上卖的调料都是用榨菜的根做出来的,便更吃不出酸了。读书的时候,最爱的是润园食堂的酸菜鸡,点菜时和服务员叮嘱上不要辣,端上来的.酸菜鸡便是真正的酸,够酸,也够下饭。一次在食堂里看见几个外国的留学生,点了几桶酸菜鸡,边吃边点头。
甜,常常有人说苏南人爱吃甜,这是真的,有次在苏州吃的鳗鱼,是那里的地方特色,很甜很香,很好吃,我一个人吃了好几段。苏南人里最爱吃甜的怕是无锡人,据说无锡人什么菜里都爱搁些糖,大学室友吃了南京的菜没放辣椒都说辣,怕是平日家乡菜偏甜所致。 锡帮菜里我最喜欢的是酱排骨,本来小排骨烧好了以后味道就香,再浇上甜甜的酱汁,味道极佳。重庆菜平日里我们只说辣,但是辣里也会有甜味。重庆的粉蒸肉,下面要放上红薯,红薯蒸了以后和米粉混在了一起,里面还放了辣椒,甜中带辣,说不出的奇妙。
苦,说到苦味,便不得不提茨菇。小时候常常看见爷爷奶奶拿着一毛钱的硬币刮茨菇皮。长辈是很喜欢吃茨菇的,但是我不喜欢,因为味道有点苦,真心觉得还没有土豆好吃。家里那时候常做的菜是茨菇肉片,我是只吃肉,茨菇碰都不碰。 后来读了汪曾祺的《咸菜茨菇汤》才对茨菇有点兴趣,家里买的时候吃过几口,依然觉得苦,实在是吃不下。百合干虽然苦,但是家里人煮的时候都会放上冰糖,吃起来苦,但是汤是甜的,吃一口百合,再喝一口汤,没几下一碗就吃完了。
辣,我以前挺爱吃辣的,那时候流行的是统一的“来一桶” 方便面,当时味道单一,只有很辣的牛肉面,有时候一顿饭就是一桶面,吃完以后嘴唇辣的生疼,浴室里洗澡受到热气都有热辣的感觉。重庆和四川菜其实并不算辣,只是麻,重庆的花椒鸡,满满两大盆,都是花椒,吃起来很麻,但是很香,一吃就不能停,越吃越辣,越辣就越想吃。有次去成都出差,客户招待的是一盆肥牛,看上去清汤不辣,其实里面放满了花椒,吃一口辣的不行,大冬天,辣的全是汗。湘菜是真正的辣,那时候去吃了湘菜,木头排骨,真是干辣,辣的鼻涕眼泪都下来了。
咸,扬州人冬天爱腌咸菜,咸肉。小时候我是吃不惯腌货的,觉得新鲜的菜和肉好吃,腌制过以后味道怪怪的,有时候腌的不好,太咸,根本不好吃。每年寒假,家里常常做的菜就是咸菜烧豆腐,腌过的咸菜和豆腐烧在一起,倒不是那么咸了,就着稀粥吃。咸肉要蒸着吃才香,咸肉蒸完以后,肥肉不腻,吃起来挺香的,但是还是太咸,吃不了太多。
中国那么大,各个地方都有各自的特色,这里也只是说了一部分,《舌尖上的中国》是个好节目,如果真的要好好整理中国味道,又何止几季节目可以说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