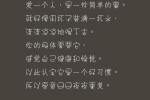清华学生的作文600字【一】
清华校园内人很多,大多都是拿着相机到处拍摄、步履匆匆的游人。校园很大,与其说是校园倒不如说是一个公园,有庄严雄伟的欧式风情大礼堂,在周围绿草地的映衬下显得格外静谧,有清华大学标志性建筑的“清华园”校门,还有风景秀美的水木清华等等,到处都能见游人在留影。陆续走了两个多小时,却还没有走完校园的一半。路边有很多卖清华纪念品的人。卖的是些书签、钢笔、笔筒之类的刻有清华字样的小物件。很多游人都停下脚步,在此逗留。
景点多的犹如浩瀚宇宙中的星辰,以至于我们没有精力,一处处仔细欣赏。只好“择优”观看。慕名而来,当然不能错过朱自清老先生笔下的荷塘。
因为是夏季,荷花正开得旺,所以才让我目睹“接天连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风采。几颗垂柳在荷塘边,压低了身段,正照着湖水梳理着飘飘长发。看到这美景,我不禁联想到了朱自清笔下中荷塘的样子:“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婀娜地开放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佳人。微风过处,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
短短的一上午,不仅丰富了我的见闻,还使我亲眼目睹了盛夏里的荷塘美景。时间匆匆流过,还不容我细细观赏,就要告别。但清华园的美景,将深深得印在我的心底,难以忘怀。
清华学生的作文600字【二】
园内有专门为游客提供的、较为人性化的服务,一是凭借个人身份证就可借得一辆自行车,二是每人只需一元钱就可乘坐校园客车游览全校。人实在是多,我们既没有借到自行车,也没有挤上校车。
幸好,这所大学是嵌在公园里的,大树很多,我们可以时不时地坐在树荫下休息一下。前面举着小旗的导游兴致勃勃地说:“清华园之名,是清代咸丰皇帝所赐。清华园原址为清康熙年间所的熙春园的一部分。
道光年间,熙春园被分成东西两个园子……”我一抬头,看见“清华园”工字厅后面的匾额题有“水木清华”四字,两旁有一副:槛外山光历春夏秋冬万千变幻都非凡境,窗中云影在东西南北去来澹荡洵是仙居。想来,这“水木清华”四字应该是出自谢叔源的《游西池》诗,“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
走过几座雕塑,充溢着荷香的清风迎面扑来,顿时感觉全身的每个细胞都得以滋润。“舒服!”弟弟说。再走几步,就有一幅美不胜收的荷塘画映入眼帘:半池荷花正在盛开,大大小小的.,翠绿翠绿的荷叶铺在水面;几位头发斑白的老者坐在池塘边垂钓。
从小就喜欢钓鱼的弟弟一见就来劲了,蹲在一位老爷爷的旁边静静地观看;几个肤色不同的游客正在兴致勃勃地摆姿势拍照;池塘边题有“风荷苑”字样的大红建筑,古色古香;白天鹅、黑天鹅、小鸳鸯、野鸭子们在水面上闲游,时而把头埋进水里捕食,时而昂起头扑楞着把水淋着全身,滚圆的小水珠从羽毛上落下来……
风从草尖滑过,画面抖动着。我也情不自禁走进了画中,坐在池边林荫下的一个大石头上,享受这令人赏心悦目的美景,想起朱自清的《荷塘月色》描写荷花真是形象,又似乎进入了张岱的《西湖七月半》里闲适文人赏荷的绝佳心境……
“妈妈……”一个约两三岁的、嬉笑着的小女孩的声音打断了我。她天使般可爱,眉间一颗小红痣,扎着一个小辫子,坐在池边,一边玩糖果玩具一边看着在钓鱼的妈妈。她妈妈每一回头对她微笑,她就拍着肉嘟嘟的小手笑。这景象让我想起西方基督教中的圣母圣子像。这母爱是人类的共性,是多么富有感染力,是多么值得称颂。
缕缕清风送来阵阵荷香,倘在静谧的夜晚,一家人伐着小船,任游湖中,该是多么和谐温馨!再想,若能乘坐在小船上,“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或许更可以领略到这半塘荷花别致的美。
清华学生的作文600字【三】
清华,你好!
和你的故事要从头说起,虽然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开头可言。2008年,我参加自主招生考试,被清华降分录取。夏天自己拎着大包小包来学校,报道的地点已经有媒体围追堵截,要求我畅想校园生活,我那时说“记录生活的日子结束,生活开始了。”——奋不顾身飞蛾扑火,有“时间开始了”的自我感动劲儿。
如今我已大三,却还没有真正融入校园生活。现在在学校还常常迷路,同学讨论的成绩与保研,我也一头雾水。嘟嘟囔囔对学校的不满却说了很多,拿人不手软,吃人不嘴短。时值百年校庆,我想说给学校的,也不是感恩与颂圣,只能硬着头皮继续怨言。
因为身在学校,所以不能仅抱怨些片儿汤的话。白衣飘飘的年代没了,就别再紧紧拽住时间的裙角嗫嚅***;学术之不知礼之不存,也已经没有再捶胸顿足的必要;大师离去,微斯人吾谁与归。大势如此,学院当然不能幸免,所以也别再长歌当哭了罢。
然而,除去以上这些,我对大学仍有抱怨,仍有不满,仍有震恐,仍有大惊小怪,仍有不情之请。
大一、大二的时候,我喜欢拽着人聊时事。我的同学们总是左顾右盼坐立难安,一副盼着人把他们解救走的样子,实在被逼急才敷衍笑道:“社会就是这样的。”我那时还觉得奇怪,二十出头正是对社会敏感的时期,即使是纯生理上也应有些喷张和兴奋,可他们是如此漠然或畏葸。
现在我发现,他们并不是漠然,我的同学们不是不关心,清华人是可爱的,愤青少,领导多,内心大概还是有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悲壮,表现出来却是高屋建瓴,虚头八脑的……模样。
陈冠中的小说《盛世》里有个叫做韦国的青年人,他说:“我今年已二十四岁。二十岁那年我做的十年计划,正一步步实现,但我不能自满。***三十岁的时候在做什么?中共中央局五个委员之一。这样一想,我知道我要加倍努力了。”
我身边就有韦国这样的年轻人,这也不难理解,北大清华的学子一路都是教育和体制的少年既得利益者,成熟了,自然也是要沿着同一轨迹,而不能跌落到食物链的底端。于是,大学成了掠夺资本的地方。
我曾经旁观过学校的干部们做事,与教育和世俗标准下少年得志的成功者打过交道,他们青出于蓝地运用官场技巧与规则,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天真与成熟、愚昧与清醒、单纯与复杂、糊涂与揣着明白装糊涂,我无法分辨他们是哪一种,也无法分辨哪种更可怕。
百年校庆快到了,逢此盛世,锦上添花的话也不缺我一个人来说,泼冷水却是我所擅长的。往小了说,“母校就是你每天骂八百遍,但不许别人骂一句的地方。”往大了说,“为何我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那么,就此搁笔,是动情是矫情,就听收信人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