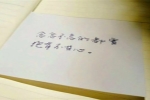写美好祖国风景的作文【一】
我们家乡的大凌河,一年四季都很美丽。
春天,小草从地里探出头来,柳树抽出新的枝条,树枝上的小鸟叽叽喳喳的叫着,仿佛在说:“春天来了,春天来了。”
夏天,天气炎热,小狗热得吐出舌头,蝉“知了、知了”地叫着,仿佛在说:“热死了,热死了。”但如果来到大凌河畔,你就会感觉到天气不那么热了。这里微风习习,十分凉爽。
秋天,河岸上风景树的叶子掉了,一阵微风吹来,叶子漫天飞舞,好像许许多多的黄蝶在飞。有时下几阵蒙蒙细雨,大凌河又像是被一层轻纱笼罩了。
冬天,大凌河更加美丽了,河水冻冰了,洁白一片。有时下一阵大雪,小孩子有的在堆雪人,有的在打雪仗,还有的在做碉堡,银铃般的笑声在大凌河上不断回响。
我爱家乡,更爱家乡的大凌河。
写美好祖国风景的作文【二】
2014年仁川亚运会女子跳马比赛的赛场上,39岁的乌兹别克斯坦老将丘索维金娜以14.750的分数获得银牌。当全场为她响起掌声的时候,每个人庆祝的是她所完成的,一个来自母亲的承诺。
丘索维金娜出生于1975年,16岁时便代表着独联体夺得了世锦赛女团和自由体操金牌、跳马项目的银牌。1992年,她同队友一起问鼎女团冠军。此后的1996年亚特兰大、2000年悉尼、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她都身披战袍,代表乌兹别克斯坦征战奥运。
实际上,丘索维金娜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之后,曾经选择退役。三年后大儿子阿里什出生,然则不久后阿里什被诊断出白血病。高昂的医疗费用逼着丘索维金娜再度出山。她说:“一枚世锦赛金牌等于3000欧元奖金,这是我唯一的办法。”
在赛场上,她从未隐藏过自己的动机就是挣钱。一个为了儿子筹钱治病的母亲,不断训练、到处比赛;曾经身为摔跤运动员的丈夫放弃了事业,专心照顾儿子。
重返赛场后的丘索维金娜迅速调整状态,2002年世界杯总决赛斯图加特站上,她夺得了跳马金牌。一年后在世锦赛上,她获得了首枚世锦赛的个人金牌。有人将这枚金牌看成梦想实现的标志、或是国家荣誉的集成。然而对于丘索维金娜来说,她不过是想延续儿子的生命,在同死神的拉扯中,占得一点点优势。
赛场上的顺遂并未换来儿子的明显好转,由于国内医疗条件的限制,丘索维金娜挥别乌兹别克斯坦,举家搬迁德国。事实也证明,来到德国确实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2008年她第五次征战奥运会,身披德国战袍的她,斩获银牌。那个晚上,33岁的丘索维金娜在一群年轻女孩中显得格外沉静,特别。
她第五个出场亮相,选择了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姿势——丘索维金娜跳,沉沉呼出一口气,稳稳起跳,完成空中动作之后,稳稳落地。当掌声响起的时候,这位母亲赢得了来自整个世界的尊重。她曾对孩子说:“你不痊愈,我不敢老。”现在,儿子的病已经逐渐痊愈,而她依旧如此年轻澎湃。
“在33岁,依旧能完成这个动作。我想,我还能继续比赛。”丘索维金娜这样告诉全世界。如今她剑指里约,即将进行她第七次的奥运征程,41岁的她被人称为“体操活化石”,但谁会否认她的动人呢?
现在我是为了自己而练习体操。对我来说,体操就像是一份工作,我就像是遇到水的鱼。——丘索维金娜
写美好祖国风景的作文【三】
人们都说:“雨山湖风景甲诗城”,我们乘着游船,荡漾在湖面上,来游赏雨山湖。
我看见过波涛汹涌的长江,游赏过无边无际的大海,但雨山湖的水令人目不暇接。雨山湖的水真绿啊,绿的像一块碧玉,雨山湖的水真清啊,清的可以看见湖底的石头,游船、画舫在湖面静静地划过,几乎不留一点痕迹,湖里还有许多小鱼,有红色的,黑色的,黑白相间的……五彩缤纷,美丽极了。
我们上了岸,岸上有许多树,一排排的,像一个个坚定的士兵。树叶落在湖面上,用叶尖点着湖面,顿时湖面漾起波纹。一阵风拂过,满树的嫩叶就摆动起来,像一位亭亭玉立的少女,在湖岸边翩翩起舞,美丽极了。那些树叶一簇堆在另一簇上面,几乎不留一点空隙。
这样的树点缀着这样的湖,这样的湖倒映着这样的树,再加上园中的`繁花似锦,莺歌燕舞,人们悠闲地走在园中,仿佛走进了连绵不断的画卷。雨山湖真是诗城一颗璀璨的明珠。
写美好祖国风景的作文【四】
五月,乱窜的无头苍蝇开始嗡嗡作响。我们是不是也像它一样没有方向的苟活着或是忙碌着。
蚊子,叫嚣着不甘示弱,在阴暗里跟着起哄。我们是不是也像它一样血液里有种夜猫子的精神,但充其量只是有张尖牙利嘴,充再多依然显得骨感。
灯影里,那鲜红的篆刻静静地躺着。曾给它取名叫做三生石,如今只是可惜了这块石头。
蚊帐里,一个人光着身子像死人一样静静地躺着。一会儿他又翻来覆去,躁动不安,原来躺着的`只是他的灵魂,有本书把它叫做死魂灵。
月光里,一切都不温不火。所有美好的东西在这里温存,或许美好害怕明天不美好,在这里停下了脚步,只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夜,不是那么平静。扇叶转动声,突如其来咳嗽声,小猪打鼾声,大象磨牙声,你听,有一只不一样的动物,在操着一口流利的乡音说着无人知晓的梦话。
夜,又是那么平静。仿佛除了心是热的,其它都是凉的。
回头望见,那些蓝色圆珠笔的文字星星点点,想要拾起,却被过去掠走了由头。
留言里听见,那些不经意的碎碎念,不造作的窃窃语,想不起还想,却被***稀释了情境。
我曾想,我是该拿小学时语文教科书里的那张颐和园的插画来比照眼前的天水一色,还是该从岸下蓝色遮住了绿光的风流的湖水回忆起不知去向的小学时的语文教科书。
不去想,如此,算是刚刚好,犹似微醉掩盖了失落。
一座城很想拥吻一座城,但它总是惯性地惧怕,那远远的冰冷的距离。征服了畏惧,却因缘灭消弭了勇气。
一座城吻上一座城,近景淹没了全城万象。梦,奋斗拓印出菁华烂漫;想,美好如此深深痴狂。
如此美好,夜让疲惫忘了倦意,我觉得意犹未尽,索性往下写,已濒临夏日的黎明。可我还得终了这个尾,又不能草草了了。可我还得画上个圈,又不能带上诅咒的枷锁。
如此美好,夜让浮躁不再升腾,我以为心如止水,任性走下去,又遭遇末路的囧境。可我仍自我拉扯,剔除我的不知薡董。可我仍俯仰寻索,发出美好的祈愿。
写美好祖国风景的作文【五】
中国人通常都信奉“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或者说在我们眼中,最可惜的不是永远拿不到冠军,而是永远差那一小步。连续三届奥运会,十二年过去,马修·埃蒙斯始终都在步枪三姿决赛的最后一枪错失机会。《费城日报》曾说:“这是永远没有尽头的噩梦。”然而对于马修·埃蒙斯来说,这只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如此轻描淡写。
2004年雅典奥运会男子步枪三姿的决赛开始,埃蒙斯一直处于领先状态,只要发挥正常,金牌就将在一枪之后飞到手上。然而命运仿佛在开玩笑,他一枪打到别人的靶子上,将金牌拱手让给了中国老将贾占波。
BBC曾经说:“这也许是最倒霉的美国运动员了。”
四年之后,北京奥运会他再次遭遇滑铁卢,比赛伊始他依旧独占鳌头,仅仅需要6.7环以上的成绩就能够抓到胜利的橄榄枝。最后时刻,埃蒙斯集中精神,将手中的枪慢慢抬起……但,没有想到这次真的手滑,他仅仅打出了4.4环的成绩。
《纽约时报》评价说“这种情况下,业余水平才会低于8.0环。”然而埃蒙斯说:“这是自然的.怪诞(freakof nature。”伦敦奥运会上,他又一次“优势失金”,有的时候,命运真实一件让人捉摸不透的事情。
不过,在他第一次失去金牌的时候,他结识了妻子捷克射击运动员卡特琳娜。当时,卡特琳娜作为解说员目睹了埃蒙斯丢金的全程,“我替他遗憾,我要告诉他这没什么大不了的”,这是他们相遇的开始。
马修曾经说过:“如果早知道,在奥运会上脱靶能够认识卡特琳娜,我第一枪就会选择打偏。”北京奥运会的决赛上,当埃蒙斯再次失去金牌,卡特琳娜轻轻地抱着自己的丈夫。埃蒙斯沉默不语,身旁的姑娘安静坚定地站在他身旁。
2010年,马特·埃蒙斯被诊断出癌症,摘除了整个甲状腺。他的朋友说:“马特对于疾病的态度,才是真正的奥林匹克精神。”生病之后的他对于一切显得更加淡然:“其实现在的生活没什么不同,也就是每天早上要吃点药,为了一个我根本就没有的甲状腺!”
他是一个熬过了“失金”和“癌症”的奥林匹克运动员。或许这就是竞技体育应该更为闪光的地方,比赛的胜利可以有很多种,在生活中赢得自我的胜利是一种。奥林匹克精神延伸出了多维的衡量标准,是一个立体的“胜利”概念。所以,远方捷克的小径上,马修和妻子的身影显得格外美好,今年他再度征战里约,我们可以怀抱着美好的祝福,希望他能够获得自己想要的那份胜利。
我热爱我的事业,这是体育精神的核心。这一切同金牌无关,我已经获得了足够多的胜利。如果说明天就让我退休,我也可以,但如果你可以前进并且展翅高飞,用你曾梦想过的姿态胜利,那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马修·埃蒙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