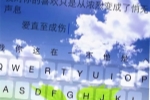坚持真理作文事例【一】
记得那时四年级下半学期,我下课后在楼梯上追逐打闹,一不小心,摔了个大跟头, 疼得我连步子都迈不开了。爸爸知道后,连忙带我去看医生,医生说是软骨扭伤了,爸爸十分着急:“俗话说的好‘伤筋动骨一百天’看来这下得好好调养几天了。”于是,二话没说,就拨通了黄老师的电话,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并向领导请了很久的假。
自从爸爸把我从医院接到家后,他每天都无微不至的照顾我,关心我,我需要什么,他总是在第一时间给予我,平时不怎么下厨的他还特地熬大骨头给我吃,甚至晚上要亲眼看着我入睡,他才放心,第二天,我发现爸爸的眼睛布满了血丝,心想他一定是晚上没有休息好。
一周过去了……
星期一,爸爸开车把我送到学校,并亲自把我背到教室 ,还再三叮嘱我千万不要乱跑。晚上,爸爸来接我,还把我从一楼背到五楼, 到家时,我看到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额头以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第二天,妈妈不停的把菜夹给爸爸,让他多吃些,这时我才发现,这几天下来爸爸真的瘦了,看着他,我的眼泪不禁流了下来。
以前,我从不知道父爱是有味道的,但我今天才知道,父爱是甜的!
坚持真理作文事例【二】
那时,我是一个不懂事的女儿。
时间的推移,岁月的流失,让我明白了许多,但我依然无法参透那本叫作父爱的经。父亲是不大爱说话的,他不喜欢笑,尤其是对我。在记忆里,父亲不会主动地抱我,不会主动地和我开玩笑,不会主动的陪我逛街……太多太多的不主动,让我和父亲的距离越来越远。我以为父亲会这样一直忽视我,然而却没想到原来这一切都原于我,原于我的任性,我的自私。在学校有整整一个月了,好想听听哈哈哈声音,但那头却传来了父亲嘶哑的声音,我开始踌躇,正不易如何是好时,他说:“和***说话吧。”顿时,我的心放松了,却莫名多了份惆怅,原来父亲还是不爱和我说话阿。片刻,电话那头传来妈妈兴奋的声音,问东问西的,大到学习小到天气,没有一个漏掉的',我的心一下子温暖起来。“让她多穿点衣服,近几天会降温;让她多喝点水,别生病了;让她别怕花钱,没钱我明天给她送去……”电话那边忽然想起了父亲的声音,低低的,但是很清晰。我颤抖地问:“妈,爸今天怎么这么多话。”“他呀,你没吃打电话都这样,习惯了。”我愣愣的挂了电话。脑中仍回想着母亲的话,原来父亲一直都不曾忘记我,只是固执的我一直都未曾发现。
轻轻翻开那本落满灰尘的画册,注视着那个高大的男人。岁月里,由她抱着我灿烂的笑脸,由她在我生病时担忧的眼神,由她想叫住我而犹豫的眼神……只是不懂事的我将它挂上了锁,才落了如此多的灰尘。今天擦亮它,放在书桌上,心里一下子充满阳光。
坚持真理作文事例【三】
无论是科学家,还是追求各自信仰的.人们,我们都在寻找真理。然而真理又就有绝对性和相对性的辩证统一关系,人们在一定条件下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认识是有限的,任何真理的认识都是对整个客观世界某些领域、某些事物和过程在一定范围内的正确反映,但也仅是对特定的具体事物在一定程度、一定层次上的近似的正确反映。我们认为真理是客观存在的,承认它可能存在的片面性,进而不断的探索与更正,不断证明、改进或者反驳已提出的真理,并对其进行公开检验,这样的探究无论是科学的、技术的、社会学的、哲学的还是文化的,都会随时间而自我更正。
任何真理都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认识,人类的认识能够正确认识无限发展的物质世界,每一个真理的获得, 都是对无限发展着的物质世界的接近。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对各阶段具体过程的正确认识总要受到实践水平及各自不同立场、观点、方法、知识水平、思维能力等因素的限制,是对客观世界的近似的、不完全的认识。因此,真理未必一成不变,追求真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很难快速地完成。往往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反复过程才能形成对事物真理性认识。
有些人认为“真理不是个人认可的,而是社会上多数人认可的东西。”这种认知是有局限性的,某种认识是否是真理,并不在于承认人数的多少,而在于它是否符合客观实际。例如,在天文学发展历程中先后出现的地心说与日心说。地心说最初由托勒密提出,在以后的一千多年里,地心说被世人奉为经典,后来更被教会所利用,成为上帝创造世界的理论支柱,为大多数人所认可的真理。之后,科学家们经过长期的探索与观察,发现行星运行规律与托勒密的宇宙模式不吻合。于是一些科学家修正了托勒密的宇宙轨道学说,但是都没有成功。后来,哥白尼发现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距离从地球上观察行星,每一个行星的情况都不相同,这是他意识到地球不可能位于星星轨道的中心,提出了日心说。尽管日心说具有它科学性,仍然很少受到人们的关注,支持者更是非常稀少,它从被哥白尼提出到最终为世人接受,期间的斗争一直持续了三个世纪,最终证明它具有真理性。
我们应当理性的对待真理,秉持科学探索精神,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实事求是、尊重规律的严谨态度,尊重科学,敢于质疑批判,在实践中认识和发现真理,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进而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坚持真理作文事例【四】
我的爸爸是个雕花匠,今年正好四十。他的年龄不算大,但白头发比我奶奶还多,一根根的很剌眼。
爸爸每天起早摸黑地工作,他敲鎯头的声音常常融进我的睡梦中。晚上,他总是很迟才睡,一上床就入梦乡,鼾声四起。
尽管工作很忙,但爸爸很关心我的学习。每学期开学前,他总要去新华书店,精心挑选后买回来一大堆练习题。为此,我曾多次在心里抱怨:这么多习题,我什么时候才能做完?
在平时,我做好练习,爸爸总要亲自批改,划下他认为重要的概念,圈出我做错的题目,给我分析错题后,又将错题剪下来,贴在错题本上,说是要我到初三中考前再做一次。
每当期中和期末考试,爸爸就更忙了。考试前他一定会问我今天考什么科目,并叮嘱我:“考试时千万别紧张,平时考了那么多次,成绩都不错,这次也一定会考好。”回来后,他会急切地问:“考试难吗?有没有什么题目不会做?作文题目是什么?”然后,他会叫我估计一下总分。看他投入的情状,好像比我自己还关心这次考试。要是我考得好了,爸爸会高兴得几天睡不着觉。要是考得不好,爸爸会帮我找差距,找原因,鼓励我振作精神重新上路。
在拿成绩报告单的前一天,他总会打电话给班主任,问各科成绩和在段里的排名。对此,我不以为然:“这么急干什么?明天到学校里去不就知道了?”
暑假里,爸爸又将我送到城关镇学习作文。每次,他用摩托车将我带到城关镇,又匆匆赶回家去干活。望着他回去的背影,我心中酸酸的。
后来,我才知道,爸爸是想让我考进嵊州一中,然后考上一所名牌大学。知道这些后,我为我以前有些想法而自责。
父爱就像海那样深沉,其表达方式总是寄寓于默默的行动中。
写到这,爸爸的形象又浮现在我面前,一根根白发是那么的剌眼。
坚持真理作文事例【五】
那是一种怎样的奇思,会将真理埋没在幽僻的山谷,若不是有夸父追日的决心,怎有人能将它觅到。那是一种怎样的悲哀,是洛阳古道上响彻云霄的感叹,还是阮籍穷途惊天动地的恸哭;是哈姆莱特站在崖边生存或者毁灭的抉择,还是千里孤坟,昭君幽咽琵琶的怨怒。我不知道亲缘对我意味着什么?莫不就是我的姓氏和血统。那么真理又意味着什么?难道仅仅也就是一种痴迷的执著。我不知道“文敌诗友”的白居易、元稹是怎样作出这种两难的选择,更无法想象那个为江州司马惊起的大诗人怎不受到“文敌”的牵绊,反而泪溅湿青衫。我不解爱因斯坦和波尔为什么开始还争得面红耳赤,转眼间又坐在一起谈笑风生。是情感埋没了真理,还是真理在情感的簇拥下熠熠生辉。这真是一种无助的悲哀和孤独。我是我父亲的儿子,而我却认为父亲的处世过于圆滑。我是我老师的学生,而我却认为老师的教学过于呆板。
我理解父亲的苦衷,更尊重老师的劳动。但“真理只有一个”,我只能选择这惟一不让我感到心疚的东西。浩渺的星空呀,你永远闪耀着动人的`灵光。你哪里知道纵使万丈的火山灰能掩埋整个的庞贝古城,却永远也掩埋不了真理的曙光。罗马广场上空激扬着令人振聋发聩的文字:“未来的世界会认识我的价值……”躁动的人群中回荡着为和平、为真理护卫的前以色列总理拉宾的声音:“相信我,千万人呼喊的声音比不上一个在战争中失去了儿子的母亲的痛苦……”
对面不是血海深仇的死敌吗?为什么明知危险重重还要执著主动伸出和平的双手?这里不是满目疮痍的子民吗?为什么还要背着激进的青年,迈出寻求和平的出路?激进青年的爱戴难道比不上对手的停战吗?亲亲子民的情感难道比不上与“敌人”的一个握手吗?“真理只有一个”,原来这就是答案,是我寻寻觅觅、魂牵梦绕的唯一的归宿。也是千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终身追求奋斗的唯一终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