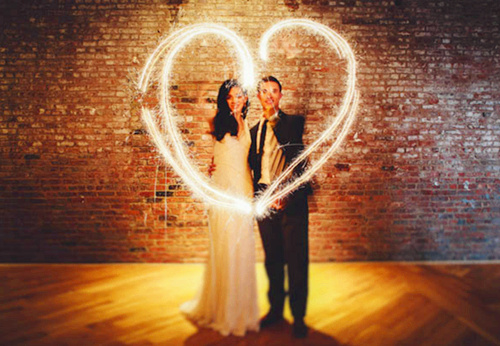
英语一篇作文要写几句话【一】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难忘的话有很多很多,就像一串泡泡,数也数不清。有批评、有教育、有表扬……这些话也像人生的酸、甜、苦、辣、咸。虽然很多话免不了时光的冲刷、岁月的轮回而逐渐被遗忘掉了,但是有些却不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消遣。其中,有一句话一直让我难以忘怀。
记得那年我七岁去上“昂立新概念”的时候,课前考试没复习,所以只考了七十九分。放学时,我愁眉苦脸,手直挠着头。因为妈妈说过,如果考试没有考到九十分以上,就要抄语法五遍。于是,我为了能骗过妈妈,就想出了一条“妙计”。
回到家里,妈妈问我考了几分,我故作欢喜,但也有点紧张地说:“我考了九十分,但是卷子掉学校了!”没想到妈妈的微笑一下子变成了密布的乌云,皱着眉头对我说:“是吗?真的吗?”妈妈似乎知道了我在骗人。我的腿有一点发抖,但仍坚持说:“是……是的!”
妈妈拿出手机,给我看了老师发来的成绩,然后语重心长地对我说道:“沈叙,你已经一年级了,不能再骗人了。考的不好就要努力去复习。一个谎,往往要用无数个谎来圆。”我听了妈妈的话,羞愧难当,恨不得找一个洞里钻进去。于是,我乖乖地走进房间抄语法和概念,还背、默了课文。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终于又取得了好成绩。
从那以后,我的脑海里经常会出现“一个谎,要用无数个谎来圆”这句话。我知道,从此我不会再去说谎骗人了,因为妈妈的这句话已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时刻鞭策着我。
英语一篇作文要写几句话【二】
有个朋友问我:“无产阶级的故事你会写么?”我想了一想,说:“不会。要么只有阿妈她们的\'事,我稍微知道一点。”后来从别处打听到,原来阿妈不能算无产阶级。幸而我并没有改变作风的计划,否则要大为失望了。
文人讨论今后的写作路径,在我看来是不能想象的自由——仿佛有充分的选择的余地似的。当然,文苑是广大的,游客买了票进去,在九曲桥上拍了照,再一窝蜂去参观动物园,说走就走,的确可羡慕。但是我认为文人该是园里的一棵树,天生在那里的,根深蒂固,越往上长,眼界越宽,看得更远,要往别处发展,也未尝不可以,风吹了种子,播送到远方,另生出一棵树,可是那到底是很艰难的事。
初学写文章,我自以为历史小说也会写,普洛文学,新感觉派,以至于较通俗的“家庭伦理”,社会武侠,言情艳情,海阔天空,要怎样就怎样。越到后来越觉得拘束。譬如说现在我得到了两篇小说的材料,不但有了故事与人物的轮廓,连对白都齐备,可是背景在内地,所以我暂时不能写。到那里去一趟也没有用,那样的匆匆一瞥等于新闻记者的访问。最初印象也许是最强烈的一种。可是,外国人观光燕子窝,印象纵然深,我们也不能从这角度去描写燕子窝顾客的心理吧?
走马看花固然无用,即使去住两三个月,放眼搜集地方色彩,也无用,因为生活空气的浸润感染,往往是在有意无意中的,不能先有个存心。文人只须老老实实生活着,然后,如果他是个文人,他自然会把他想到的一切写出来。他写所能够写的,无所谓应当。
为什么常常要感到改变写作方向的需要呢?因为作者的手法常犯雷同的毛病,因此嫌重复。以不同的手法处理同样的题材既然办不到,只能以同样的手法适用于不同的题材上——然而这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经验上不可避免的限制。有几个人能够像高尔基像石挥那样到处流浪,哪一行都混过?其实这一切的顾虑都是多余的吧?只要题材不太专门性,像恋爱结婚,生老病死,这一类颇为普遍的现象,都可以从无数各各不同的观点来写,一辈子也写不完。如果有一天说这样的题材已经没的可写了,那想必是作者本人没的可写了。即使找到了崭新的题材,照样的也能够写出滥调来。
英语一篇作文要写几句话【三】
“无论做什么事情,从事什么工作,都得尽职尽责,因为这是老师和同学们对你的信任。”李老师意味深长的话语又响在我的耳畔。不知为什么,李老师说了好多帮助我学习的话,唯独这句话让我始终难忘。
记得上四年级的时候,李老师见我学习不错,组织能力也过关,就让我当了个小组长,官不算大,每天收八个人的语文作业,然后认真检查,写得烂的让他重写,最后上交给老师。
可是,纸是包不住火的,终于有一天,早读的时候,李老师让我到外面去,我的心“咯噔’一下,觉得情况不妙。李老师等我走出教室,自己也跟着出来了。她拍了拍我的肩膀,脸上露出了慈祥的笑容,说:“最近,我发现你们组的作业质量有些差劲,你是组长,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呢?”“这……”我无言以对。
老师拿了一本作业,对我说:“这个同学是你们组的,你自己看看吧。”说着,老师脸上露出严肃的表情。我的心里就像揣了一只小兔子一样,嗵嗵直跳,看着那本写得一塌糊涂的作业,我羞愧极了。李老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无论做什么事,担任什么工作,都得尽职尽责,因为这是老师和同学们对你的信任。”我使劲地点了点头。
这句话让我始终难忘,每当我极不耐烦,想应付了事的时候,就会想起这句话,它一直鞭策着我,鼓励我做好每一件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