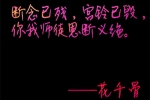选择就业和创业的英语作文【一】
人要回到人自身,回到本真的家园,这个目标不是科学理性能够实现的,重返家园只有诗歌才能靠近。海德格尔用了“靠近”而不是用“抵达”进行描述,也就是表明永远都处于“在途中”的状态。叶世斌的诗集也叫《在途中》,这本诗集站在存在主义的哲学起点上,以诗歌的方式对人的存在方式及存在的可能性意义进行了一次个人化的追问与探索,并完成了由存在主义到人道主义诗性哲学的嬗变,从而确立了一种不愿放弃终极的诗歌品质。
海德格尔把诗人看成是“人和神之间的使者”,站在人和神之间的诗人,虽然看不到神,但能看到天空,诗歌是对天的仰望,在仰望中捕捉到了神的信息,概括地说来,由于诗是以个人化而非公众化的情感体验领悟着生存赋予人的痛苦、欢乐、收获、幻灭、光荣、耻辱等种种事实,由于诗的“非他人化”、“反推理性”、“拒绝真理过滤”,是一种真实可靠的吟咏,因而聆听到了神的声音,感悟到了神的喻示,呈现了本真的存在。康德认为人的隐藏的判断力是超越纯粹理性和实验理性之后的审美和艺术经验,海德格尔的进一步总结认为就是诗。所以真正的“诗性”就是一种“神性”。
叶世斌的诗集《在途中》对生命、人格、尊严、价值、意义的追问和探索与存在主义哲学最先形成的是内在结构上的对称,这不是诗人选择的结果,而是精神上的默契。诗中的悬空、无根、沦陷、沉没、失踪、幻灭的意象密集地埋伏在稿纸上,反复引爆,开山凿石般地炸开前行的路。叶世斌“在途中”不只是为了抵达,而且是在途中不断寻找“路途”,在途中的自我批判、反省、救赎中一路跋涉,最终立足于人道主义的城垛上眺望家园和神的居所。
人之“在世”是因为“站出了自身”,“站出了自身”就是站出了动物性生存,于是就有了时间和空间的选择,就有了意义和终极的要求,这是人的自由,也是人的灾难。人之“在世”的方式注定了人必须面对两种存在可能:一个是本真的存在,一个是非本真的存在。然而人在本真和非本真的夹缝中却被剥夺了选择权,人的悲剧就在于你根本就不能超越力量强大的非本真生存,比如公众意志、日常行为、传统方式、流行观念是根本不让你超越的,而且是集体认同的真理。所以“此在”的人把“自己”交给了别人,把自己交给了“日常”,自己不再是自己,日常的自己是假冒的自己,是名誉的自己,海德格尔称做“日常自己”,或“他人化”的自己,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买衣服逛商场并不是逛自己,而是逛别人能够接受的自己,说话做事的合理性是别人认为的合理性,而不是你自己的合理性,所以诗人为什么要眺望童年、湎怀丢失的时光与风景,因为那里保留着没有异化没有被分裂的本真,那里有着神性的光辉。
叶世斌的《在途中》与前两部诗集《门神》和《倾听与言说》有了很大的不同。高强度的情感爆发力和尖锐的感觉穿透力是叶世斌诗歌最显著的特质,而其诗歌的视点前后却有着明显的差异,前期的诗歌气质中流敞着尼采、叔本华的血脉,用焦虑、绝望的内心体验着荒诞和荒谬的存在如何将“自己”挤压、异化、分裂,是由内向外的透视和撕裂,是内心演绎的存在,更多是臆想、放大、虚拟的存在;而《在途中》的相当一部分诗中,虽继续坚持着早期既有的对生命、对存在的性质认定,而视点却转换成由外向内的递进,即由客体的事实引发内心的自省与审判,“由我而事物”到“由事物而我”,这种转变在诗歌形式层面上几乎很难看出来,但它在另一个意义上昭示了诗人和诗歌更逼近形而下的存在,更强化了内心的质感和体验的具象,通俗地说,是具体的生活在诗歌中下沉,而不是用诗歌发酵一种臆想的生活。这样阐释是要说明叶世斌的《在途中》与荷尔德林的《归家》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是诗歌的哲学,一个是哲学的诗歌。从阅读对诗的期待来说,人们愿意读到诗歌中的哲学,而不愿意读到哲学中的诗歌。
诗歌的本质是抒情,诗歌抒情的高贵性在于高端体验中翻译了不可言说的生存真相,唯有诗才能逼近本真的生命,这是诗人骄傲的根据所在。在全面技术化和物质化的时代,人被挤压到存在的边缘,人注解着物的存在,物是人的尺度,物本主义消解了人本主义,就像《鸽子一直传输和跟踪我》一样,物化了的手机屏上的“鸽子由来已久/一直传输跟踪我/悉知我的快乐,愤怒,恐惧/和鲜为人知的秘密”,“我不时地望着它,感到惶惶不可终日”,不只是传输和跟踪,还有隐形的警告和随时发生的出卖。在《我是一个被雷击的人》中,“我”已被电控制了全部的行为,电成了另一种生存血液,“电流,这个世界和我的血液/输入我的每个细胞,纠缠/和捆缚我。”叶世斌以诗阐释了“人被物控制和制造”的悖反与荒谬,在人们集体被物征服之后,人们已经失去了对自身的认知能力,不知道人实际上已成了“电源”的目的,人成了电源使用价值的一个目标,潜伏在我们生活中的科技意志一天天地在瓦解我们自身的意义,删除人的本真的天性,电源接通的时候,“现代物质温暖和照耀着我们/如同这个夜晚,被白炽灯/和取暖器瓦解,构建/生活对我们的改变。”“我们迎着光亮,成为/夜晚的一种温度”,那么我们的温度在哪里呢?叶世斌以诗歌隐喻和象征的叙事体验呈现了人的下沉和主体的失踪,不谋而合了存在主义哲学中“人是有待被制造的人料”这一颠覆性的人的定义。人被逐渐纳入到科技体系内,科技的力量就重新塑造了人,人的自然性(本真性)遭遇了根本上的破坏,人异化成了物的零件。叶世斌有不少诗歌揭示了这种混淆和异化以及目的的被篡改,《花摊》一诗中,“这些争相购花的人/早已被花朵收购”,在不停追问与领悟中的诗人,极其准确地为当下的人进行了定位,这就是“客居”,当“自己”和“本真”消失的时候,人与“在世”的关系就是租赁关系,《城市和宾馆大厅的一盆竹子》中我和这个城市以及一盆竹子都是这个世界的客居者,是租赁在这块有限土地上的客居者,这里不是对生存形态的一种探究,而是对生存事实的确认。没有家园而在途中,没有本真而被悬空,所以城市、我、竹子“盘根错节/被堂皇的钢铁和水泥笼罩/被客居的虚伪和倦怠伤害”。正如《我不知道所有的租金是否偿还》中所说的,“租赁的事物令人疑心/所有成果变得沉重而残忍”,当生命和生活的全部过程建立在一种租借程序中时,“客居的虚伪把我熄灭”就是不可避免的。
“异化”之后人的存在状态表现为“客居”和“租赁”,“客居”、“租赁”下的是本真生存的“虚悬”和“失踪”,《手执火把的人》无法照亮夜晚,只能照见黑暗,“手执火把的人/被自己举着”,却“无法执掌/自己。风在火焰上摇摆/给他火势,那就是他忽然/被吹熄,或被火卷走的时候”,手执火把的`姿势成为一种虚悬和危险,就像《坐在院子里的女人》,与椅子、桂花、阳光甚至院子毫不相干,人在失去本真后成为院子里的被抽象出来的符号,亦如高天《流云》,“天空回到它的本义/还有什么比流云更缺乏根据/这悲壮的一刻不停的流云呵/匆促的无可挽回的流云/不是一场风鞭子似的/跟在它的后面,而是隐蔽在/天空深处的虚无,那永恒的/虚无驱赶着它们!已来的/未来的都将带着我们的/泪光,赶向虚无”。《找不到落点的蜻蜓一直飘着》中,蜻蜓触碰的都是“不踏实的事物”,“三十个夏天/过去,池塘和垂柳都已/枯死。那只张着翅膀的/蜻蜓,找不到落点。”没有“落点”的“虚悬”是追求终极和还原本真全面失败后的人类的共同的隐喻。现代物质挤压下的“无根”性是人类的集体困境,病毒一样的四处漫延。存在主义哲学在尼采和叔本华那里是极其悲观的,叔本华把人生过程看成是一次自***的慢动作演示,叶世斌的诗歌在另一个层面上将“自***”与“他***”纠缠着解释和体验异化与分裂所造成的生存伤害,所以他的诗中反复出现“活埋”的意象。在一首《这条临时的即将的闪电》的诗中,“摇摆的槐花,宿命的槐花/一生完成一次下落一生都在/一刻不停一去不回地抵达”,人的一生就是一次一去不回的抵达,所有的美丽与喧哗都是瞬间的闪电,如同死亡不可替代一样。在叶世斌早期的诗中,他计较着精神和灵魂失踪后的“敌人”和“对手”,并表现出了死不瞑目的愤怒与抗议,而《在途中》的存在体验虽然有着类似的哲学背景,却在诗的形态上已经表现为沧桑际遇后的从容和淡定,并且冷静地审视着一种不动声色的压迫与窒息,在《平静和亮得看不见的玻璃》、《这个夏天被堵得严严实实》等诗中已经表现出了诗人强大的承受力和直面的勇气。这一系列诗中,诗人的表达与言说不是为了算账,而是为了领悟。诗的境界明显得到了强力提升。诗歌之于哲学正在于体验和领悟,是体验领悟后的呈现,而不是实证。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诗性。应该说,《在途中》更逼近诗性的哲学,而不是定义的哲学。
人最难解决的就是孤独,人本来就是孤独的个体,在罪过与信仰,绝望与激情,生存与死亡,教堂和墓地之间,人的最大的孤独在于精神的孤独,心灵的孤独,那就是“失踪”与“虚悬”后的无话可说与无处可说,即丧家之犬的事实。存在哲学之父克尔凯郭尔在《恐惧与颤栗》一书告诉人们,并不是所有的孤独和绝望都有力量决定着你视线的方向,重要的是在路上你将何为。二十世纪神学家卡尔。巴尔特说“人类被拯救的时刻是这一时刻,只有被逼到悬崖上走投无路不得不跳下无底的深渊,这瞬间他才获得了拯救,上帝托住了他。”叶世斌《在途中》一直顽强地表现出拯救的愿望与意志,因为他知道一个诗人真正的精神***是在绝望中放弃自我拯救。上帝拯救的是那些一路餐风露宿风雨兼程的朝圣者。
存在的失真造成了距离神圣越来越远,表现在《我们因为看不清自己而美丽》这首诗中是人与雾的关系,世界是一个迷惘无边的雾境,“历史和未来,所有的事物/被雾裹着。一部分文字/拂去雾,把我们带进/更深的雾里。我们的目光/被雾围困,目光敏锐而收缩”,雾里事实是不可翻译和言说的事实,是接近了最本真的事实,用诗来表达就是“美丽”的事实。日常的生存被公众理性、传统世俗、集体规则反复过滤和篡改,这使我们遗忘了自身的由来和出处,“因为什么,我把/绝世的真情/谋***?遗忘抽象着往昔/橡皮一样慢慢擦去/疼痛,罪恶和灾难”(《遗忘是一种精神还是一种能力》)遗忘的过程是失真的过程,也是自***的过程,诗人不能容忍底线失守,于是自省、自审、自救就成了叶世斌诗歌的重要方向。
“走近上帝的是/是哪一种鞋码?它怎样/错开车辆,蚁虫和自己”(《父亲和我正陷在途中》),面对这不可救药的生存事实,叶世斌以诗的方式表达着找回本真,重返家园的努力。这是一次蜕化变质后的出发,是一次诗性哲学的转向。叶世斌以宗教的情怀,以人道主义的立场,开始了他的灵魂救亡的诗歌之旅,用笃定、沉稳的视角反省人被异化的灾情,以一种强烈的忏悔与救赎的态度表示了自己被异化分裂的苦痛,以及必须承担的责任。“自我”本真的丧失,除了物质和世俗力量的摧残,人自身的妥协甚至是合作加快了灵魂异化与精神分裂的速度和效率,《在生命形态的完成》中石头被塑造和雕凿的过程,就是石头被异已化的过程,“我就是一条河豚,以毒性?和自虐为生,不可救药”(《自虐的河豚》),人在很多时候,是靠繁衍毒素为生的,而不是靠信仰和神圣活着的,比如以毒攻毒,以恶制恶,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仇恨和敌意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精神质地,这使得人不仅自己远离了神圣,而且还制造了“在世”的焦虑与恐惧。物化的世界里,我们不仅对神是有罪的,对自己也是有罪的。叶世斌诗中以“故居”的意象表达了原初纯净的家园,表达了失落和丢失“故居”的愧悔,那不只是追忆,而是在追忆中的精神重返。“故居”保留着岁月的真相,“故居的石阶知道我的鞋码/不知道我出门后的走向”,出门后的人注定了像兔子一样穿行,焦虑、恐惧、紧张、分裂、异化不属于故居台阶上的“我们”,我们努力地与这个虚假的世界进行合作,同台表演,当我们被雕塑成形的时候,那就是本真之我的“活埋”。叶世斌当意识到客居在世的时候,便无法宽恕自己的合作和自我出卖,于是他痛心疾首地反省自己。“一些丧失把我们变成神/正如一些获得把我们变成鬼”,“我们获得很多,是因为失去更多”,在《这是木鱼》的声音中,诗人开始忏悔,“我的一生多少罪孽/如同我的心里多少泪泣/垂直的雷霆在我耳际沉默/我连自己的哭声都无法听见”,如同一只焦虑的兔子,“多少年,我面不改色/在心里流汗,在原地逃窜/偷取的自由到底多大面积/是否一片蓖叶就能覆盖我的安全”,(《穿行的兔子如同黄昏的一根白发》),诗人在忏悔与自审中决绝而坦诚,公开承认“我的命运人迹罕至”。在巨大的孤独和遥遥无期的途中,诗人内心压抑着一场揪心的泪水,如芭蕉上的雨,足以使整个夜晚泪流满面,而在归家的途中,不必倾诉与宣泄,重要的是内心修炼与皈依,修炼神性,皈依神圣,那样才会让内心安静详和。在第二辑《必须有个地方让我长跪不起》中,诗人的宗教情结和人道主义理想旗帜鲜明,并成为《在途中》诗性哲学的终点。这一辑中对生命的关怀、对脆弱的悲悯、对死亡的宽容、对亲情的珍惜,都已经超越了世俗层面的形而下的情感,而上升为一种博大的人生态度和哲学立场,《千佛洞》、《济南的佛》、《这是木鱼》、《必须有个地方让我长跪不起》是《在途中》真正能够打动人、震撼人的诗作,诗人的忏悔、悲悯、拯救、普渡众生的情感虔诚而洁净,毫无杂质,只有聆听了神的声音,才会有与神交流的可能,这不是权力,而是心力。“我跪拜而来,满含泪水/佛呵,我的心早已千刀万剐/我的一生罪孽无数。请将绝世的/磨难累赐于我以至万劫不复/但我的祈祷声声啼血:请你饶恕”(《济南的佛》),“香炷的火向下走,接近/人间。香炷的烟向上升/指向天堂。我的手抓住他的/体香,一次次被灼痛”,“必须有个地方让我低着头/长跪不起。这就是为什么/我随烟升起,在天外/把人世的真相撕破/一生跋山涉水,拯救救星/当我满含热泪,我知道/我救回了苦难和慈悲/我坐在天堂最后一级台阶上/瞑目悔悟,像在瞌睡”(《必须有个地方让我长跪不起》),至此诗人已经完成了他对人生、对生命、对意义的最后的领悟与体验。在“救我”和“救世”的双重理想中抵达到了人道主义中心高地。
保罗蒂利希说,“人对宗教的追求并非出自天性,一开始出自于困境,追求宗教信仰的前提是人生的无意义”,叶世斌的诗性哲学并不奔向宗教神学,而是弥漫着宗教情结,真正构成叶世斌诗性哲学基础的证据是,诗人从没有停止过意义追问和终极梦想。存在主义哲学是他的追问与思索的精神视点,更多的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真正契合叶世斌精神内核的是人道主义诗性哲学,悲悯、恻隐、忏悔、赎罪的精神指向直接抵达其诗歌的核心价值区域。即使诗歌呈现出的是“救世”的徒劳,但灵魂“自救”的愿望最起码在诗歌中表达或实现了,况且诗人一直还在途中,一生的努力和修炼足以使本真的家园越来越近。
选择就业和创业的英语作文【二】
凯恩斯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创始人。凯恩斯一生最为著名的就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该书被公认为20世纪最重要的西方经济学著作。他提出的“有效需求”和“乘数理论”代替了传统的经济理论,获得了经济学界的公认,并被人们称之为“凯恩斯革命”。凯恩斯凭借《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不但成为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甚至是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开山鼻祖,而且他还能被置身于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西方经济学家的行列,能与亚当斯密相提并论。
《通论》的基本内容和基本思想主要有五个方面
选择就业和创业的英语作文【三】
所谓有效需求,是指商品的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时的社会总需求。有效需求不足,是因为货币的购买力不足,并由此导致萧条。凯恩斯给出了关系等式:
收入=产品价值=消费+投资
储蓄=收入—消费
因此,储蓄=投资
选择就业和创业的英语作文【四】
《通论》的核心是就业不均衡理论。凯恩斯认为,经典经济学只承认两个失业范畴:一是摩擦失业,一是自愿失业。充分就业理论基于两大前提:第一,工资等于劳动力之边际生产力;第二,当就业量不变时,工资效用就等于该就业量的边际负效用。在古典经济学家眼中,资本主义总是处于充分就业状态,所有愿意从事劳动的人都会就业,只有自愿失业者或者正在转换就业位置的人才会处于失业的状态。
凯恩斯反对萨伊有关供给会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他认为萨伊忽略了货币这个因素。事实上,供给与需求不一定会平衡。他提出的法则是:储蓄动机与投资动机不同,人们有可能储蓄过多而消费过少,而使得储蓄和投资不一致,从而产生市场需求不足——对消费品、生产资料需求不足,供过于求,最终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与失业。
萨伊定律在西方具有很多不同的表达方式,其最简单的一种是“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意思是说,生产者进行生产,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消费,主要是为了拿自己的产品与其它生产者进行交换,以便得到他所需要的其它东西。只要社会上存在着一种供给,就会自动地存在着一种相应的需求。所以,按照萨伊的说法,社会上一切产品都能被卖掉,因此不会出现生产过剩的现象。不仅如此,由于每个生产者都尽量制造出最大数量的产品和别人交换。也就是说,社会不仅没有生产过剩的现象,而且还能使生产达到最高的水平,即达到充分就业状态。
选择就业和创业的英语作文【五】
凯恩斯认为,当就业量增加时,总所得也随之增加。然而社会往往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总的真实所得增加时,总消费量也在增加,但没有所得增加德那么快。这是一个心里法则,无论从人性来看,还是从具体事实来看,这都是毫无疑问的。他详细列举了影响消费倾向的客观、主观因素。客观因素主要包括:工资单位的改变,所得与净所得差别的改变,在计算所得时没有考虑到资本价值的意外改变,时间贴现率的改变,财政政策的改变等;主观因素则包括:人性的心理特征,社会习俗和社会制度等。
选择就业和创业的英语作文【六】
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与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是西方经济学史上三部划时代的著作。《国富论》为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奠定了基础,《经济学原理》则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为经济自由主义作了总结,而《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作为凯恩斯主义的经典之作,标志着凯恩斯主义这一独立的理论体系的形成。
进入20世纪,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加深了资本主义的矛盾,先后发生了多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特别是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企业纷纷***,大批工人失业,购买力下降,市场供求力量失衡,这一严重的现实使得新、旧古典经济学理论陷入“经济学危机”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是由于力。图挽救这次“经济学危机”而被称为对传统经济学的“革命”的。它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解决就业,以缓解市场供求力量失衡的问题。本书共分6篇24章。第一篇引论中,批评了李嘉图及其以后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约翰、穆勒、马歇尔、庇古等人的两个“前提”:
一、工资等于劳动力的边际产物;当就业量不变时,
二、工资的效用正好等于该就业量的边际负效用,这仅适用于一种特例,而不能适用于普遍情况。
进而他分析了“有效需求原则”:总供给函数和总需求函数相交时的数值,就业量就是这个交点值。
第二篇中,他则主要阐明了预期、所得、储蓄、投资的定义,以及使用者成本等问题。第三篇研究了消费者倾向,分析消费倾向的主客观因素、边际消费倾向与乘数的关系。第四篇关于投资引诱,分析了资本边际效率、长期预期状态、偏好与利率、资本性质以及利息与货币的特征。第五篇货币工资与物价,阐述了货币工资的改变、就业函数与物价的问题。第六篇引用了几篇短论,分析了商业循环,论述了重商主义、禁止贷法、加印货币以及消费不足论。
最后是结束语,《通论》所引起的社会哲学。而起中则是“有效需求理论”是本书最核心精彩的部分,凯恩斯运用总量分析的方法,对总收入、总需求、总供给、投资、消费、就业水平、物价水平等一系列总量相互关系进行研究的同时,独辟蹊径地创造了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定理,精辟的分析出导致现实失业与萧条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国家干预经济的主张。《通论》中我们比较认知的理论是它的有效需求理论,以及产出变动而非价格的变动的调节作用。有效需求原理认为,在一个封闭的的有闲置资源的经济中,产出水平(即就业取决于总的计划支出,计划支出包括两个部分:居民的消费支出(C和厂商的投资支出(I《通论》中没有明确分析直接由政府支出刺激。的支出变动的结果或间接由税收变动而带来的支出变动的结果。
因此,《通论》中有两个部门(居民户和厂商,计划支出由下列方程给出:收入(Y=产品价值=消费(C+投资(I。本书的核心观点是:就业量决定有效需求,也即消费,而就业量取决于消费倾向和投资量。在假定社会的消费倾向为既定的情况下,则就业量的均衡水平决定于当前的投资量。投资量取决于资本的边际效率和利率所确立的投资引诱。凯恩斯极其强调资本市场的力量,这是他高于后世货币主义者之处。货币主义者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通过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来控制货币数量,就可以控制利息率,从而促使经济稳定发展。凯恩斯却雄辩地指出,带有投机需求的货币是促使利息率剧烈波动的主要因素,投机需求主要是出于人们对未来的\'主观预测,这种预测的变化是不可能通过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来抵消的。股票、债券等资本市场在决定利息率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凯恩斯甚至早已预测到,未来央行可能不得不通过直接买入长期债券或者股票来调节利息率——这正是今天美国、日本和欧洲发生的事情。但是凯恩斯的观点带有很强的独断性,往往没有过硬的实证支持,至少在他的时代是如此。开篇的那个强硬的论断——工人与雇主争议的工资是名义工资而不是实际工资,可以说是经济学史上革命性的一页,凯恩斯却从来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论证。他提出这一点,纯粹是一种天才的直觉和感悟,并非有统计资料或清醒逻辑的支持。他在后面的章节提出,由于中介成本的存在,长期利息的最低限度是2-2.5%,这个说法也值得商榷(凯恩斯再次以“大概仿佛也许是”的方式完成了论证。这些观点对凯恩斯主义来说是基础性的,但凯恩斯仅仅以顽强的信心和天才的直觉来支持它们,所以说凯恩斯主义是建立在沙子之上的经济学。本书从伦理学、法律学与经济学方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随着形势的发展,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作出了论述。为政府宏观调控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指出了政府调控的核心目标,既充分就业。因为只有充分就业才能保证有效需求,而有效需求是经济发展的根本推动力。
各国政府多数依据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来进行各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进行宏观调控。这对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的道德建设、法制建设和经济理论研究,还是很有启发的。具体说来,至少有两点:
第一,《通论》有力地证实:市场不是万能的。由于市场中各个利益主体的经济行为不可能完全协调一致,所以经济萧条(乃至经济危机和大量失业的“市场失灵”的现象会时常存在。因此,国家有必要使用宏观调控的手段,将市场调节与国家宏观调空有机结合起来。
第二,《通论》也说明了作为宏观调控手段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应该通过何种途径来消除这些“市场失灵”的现象。
凯恩斯认为,“市场失灵”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投资不足,而投资不足所引发的收入下降又导致了消费的萎缩。货币政策的推行便是通过利息率的降低来刺激投资的增长,进而拉动消费的增长。当货币政策刺激投资增长的力度不足以完全消除“失灵”现象时,国家就必须同时使用财政政策的手段,把资金直接投资于“公共工程”等,以便扩大内需,从而达到消除“失灵”现象的目的。毫无疑问,凯恩斯是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他敢于打破旧的思想的束缚,承认有非自愿失业的存在,首次提出国家干预经济的主张,对整个宏观经济学的贡献是极大的。
他承认资本主义社会除了自愿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外,还存在着“非自愿失业”,原因就是有效需求不足,所以资本主义经济经常出现小于充分就业状态下的均衡。这样,凯恩斯在背叛传统经济理论的同时,开创了总量分析的宏观经济学。因此,在凯恩斯经济理论中,金融理论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以上就是我对凯恩斯本人以及凯恩斯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感想。虽然对该书中部分理论和表述不是十分理解,但通过阅读该书使我从中获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