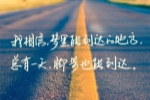生日聚会英语作文几句话【一】
从前,有一块非常骄傲的橡皮,它每天都要帮它的小主人把错误清楚,所以它以为,自己是最重要的。
一天,小主人做完作业,就出去玩了。这时候,橡皮擦站了起来,大摇大摆地向铅笔盒那走去。“快出来吧,胆小鬼们,小主人早就出去了》”橡皮擦傲慢地说。文具们纷纷走了出来。橡皮擦走到文具们面前说:“文具们,我是大名鼎鼎的橡皮擦,你们看,我香气四溢、色泽鲜艳,可是小主人身边的‘大红人’啊!”这时,一位美丽的铅笔小姐从众文具里面走了出来,彬彬有礼地说:“你好,橡$2先生,我是铅笔小姐请问可以和你交个朋友吗?”“啊!原来你就是铅笔呀!”铅笔小姐很谦虚,可橡皮擦大声说,“就是因为你,小主人粗心的毛病才会出现,要不是我……”橡皮擦不停的怒斥道。(铅笔小姐在旁边周进没哟,面红耳赤、可怜兮兮地听着橡皮擦的教训。众文具对橡皮擦的行为非常生气,铅笔盒愤怒地站了起来,一个没站稳,不小心倒向橡皮擦,吧橡皮擦给压扁了,众文具欢呼雀跃起来。
最后,橡皮擦得到了应有的下场,而铅笔小姐取代了橡皮擦的位置,成了名副其实的大红人。
生日聚会英语作文几句话【二】
在三年级的教室里,同学们都出去了,橡皮们纷纷跳出主人的书包,开始了诉苦大会。
一块橡皮说:“请同胞们帮我评评理,看看我的一身,没有一块皮是好的,我都不敢下塘洗澡了”。另一块橡皮却自豪的说:“哈哈,看看我,我在娘家时,叔叔阿姨可就喜欢我,把我的身上加了一层粉红涂料,再撒上香水,又漂亮又香香的我,主人可喜欢我了,把我当宝贝宠呢!”
“哎!我真羡慕你啊,我原本也是既干净又漂亮,可我现在身上都是窟窿。”一块满是窟窿的橡皮苦着一副脸大声的说着。
橡皮们都记着述说自己在主人那不同的经历,都希望自己的主人要善待自己,过了一会儿,一位德高望重的橡皮说话了,“别吵别吵,我们要请有文化的铅笔来帮忙吧,让它把我们的心声告诉主人吧!好让主人醒悟过来!”
当主人们回来看见铅笔写的信时,都惭愧的地下了头。
生日聚会英语作文几句话【三】
我自己从来没想到需要辩白,但最近一年来常常被人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想想看我惟一的嫌疑要末就是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三届曾经叫我参加,报上登出的名单内有我;虽然我写了辞函去(那封信我还记得,因为很短,仅只是:“承聘为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谨辞。张爱玲谨上。”报上仍旧没有把名字去掉。
至于还有许多无稽的谩骂,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可以辩驳之点本来非常多。而且即使有这种事实,也还牵涉不到我是否有汉奸嫌疑的问题;何况私人的事本来用不着向大众剖白,除了对自己家的家长之外仿佛我没有解释的义务。所以一直缄默着。同时我也实在不愿意耗费时间与精神去打笔墨官司,徒然搅乱心思,耽误了正当的工作。但一直这样沉默着,始终没有阐明我的地位,给社会上一个错误的印象,我也觉得是对不起关心我的前途的人,所以在小说集重印的时候写了这样一段作为序。反正只要读者知道了就是了。《传奇》里面新收进去的五篇,《留情》、《鸿鸾禧》、《红玫瑰与白玫瑰》、《等》、《桂花蒸阿小悲秋》,初发表的时候有许多草率的地方,实在对读者感到抱歉,这次付印之前大部分都经过增删。还有两篇改也无从改起的,只好不要了。
我不会做诗的,去年冬天却做了两首,自己很喜欢,又怕人家看了说“不知所云”;原想解释一下,写到后来也成了一篇独立的散文。现在我把这篇《中国的日夜》放在这里当作跋,虽然它也并不能够代表这里许多故事的共同的背景,但作为一个传奇未了的“余韵”,似乎还适当。
封面是请炎樱设计的。借用了晚清的一张时装仕女图,画着个女人幽幽地在那里弄骨牌,旁边坐着奶妈,抱着孩子,仿佛是晚饭后家常的一幕。可是栏杆外,很突兀地,有个比例不对的人形,像鬼魂出现似的,那是现代人,非常好奇地孜孜往里窥视。如果这画面有使人感到不安的地方,那也正是我希望造成的气氛。
生日聚会英语作文几句话【四】
在外滩看见一个警察打人,没有缘故,只是一时兴起,挨打的是个十五六岁的穿得相当干净的孩子,棉袄棉裤,腰间系带。警察用的鞭,没看仔细,好像就是警棍头上的绳圈。“呜!”抽下去,一下又一下,把孩子逼在墙根。孩子很可以跑而不跑,仰头望着他,皱着脸,眯着眼,就像乡下人在田野的太阳里睁不开眼睛的样子,仿佛还带着点笑。事情来得太突兀了,缺乏舞台的人往往来不及调整面部表情。
我向来很少有正义感。我不愿意看见什么,就有本事看不见。然而这一回,我忍不住屡屡回过头去望,气塞胸膛,打一下,就觉得我的心收缩一下。打完之后,警察朝这边踱了过来,我恶狠狠盯住他看,恨不得眼睛里飞出小刀子,很希望我能够表达出充分的鄙夷与愤怒,对于一个麻风病患者的憎怖。然而他只觉得有人在注意他,得意洋洋紧了一紧腰间的皮带。他是个长脸大嘴的北方人,生得不难看。
他走到公众厕所的门前,顺手揪过一个穿长袍而带寒酸相的,并不立即动手打,只定睛看他,一手按着棍子。那人于张惶气恼之中还想讲笑话,问道:“阿sir是为仔要我登牢子?
大约因为我的思想没受过训练之故,这时候我并不想起阶级革命,一气之下,只想去做官,或是做主席夫人,可以走上前给那警察两个耳刮子。
在民初李涵秋的小说里,这时候就应当跳出一个仗义的西洋传教师,或是保安局长的姨太太(女主角的手帕交,男主角的旧情人。偶尔天真一下还不要紧,那样有系统地天真下去,到底不大好。
生日聚会英语作文几句话【五】
在四年级四班的教室里,同学们去上体育课了。橡皮们纷纷跳出铅笔盒开起了会议。
一块橡皮自豪地说:“我从橡皮厂里出来时,那里的叔叔和阿姨可好了,他(她)们给我加了一层粉红色涂料,漂亮极了!
我的小主人非常爱惜我,用完了赶紧把我放进铅笔盒里。还定期给我洗澡呢!”
“唉,我真羡慕你呀!我原本也是既干净又漂亮的,”一块满身是洞的橡皮,满脸愁容地说:“可是,落到我那淘气的小主人手里,你们看,扎得我浑身是铅笔眼儿,疼死我了!”
“呀,这真太可气了!”橡皮们都替他打抱不平。
橡皮们述说着自己在主人那里不同的经历,觉得各自的待遇真是天壤之别,有的高兴,有的难过。
正在这时,一块老年橡皮说:“我们要请铅笔帮忙,让它们给那些不爱护文具的同学写一张纸条,让他们醒悟!”橡皮们纷纷行动起来……
下课铃声响了,同学们回到教室,一些孩子找不着橡皮,哭了起来。突然,他看见了桌子上的纸条:小主人,我那么愿意为您服务,请爱惜我吧!
同学们后悔极了,他们决定找回橡皮,永远爱惜他们。
从此,橡皮们变得干净极了。
生日聚会英语作文几句话【六】
在四年级四班的教室里,同学们去上体育课了。橡皮们纷纷跳出铅笔盒开起了会议。一块橡皮自豪地说:“我从橡皮厂里出来时,那里的叔叔和阿姨可好了,他(她)们给我加了一层粉红色涂料,漂亮极了!我的小主人非常爱惜我,用完了赶紧把我放进铅笔盒里。还定期给我洗澡呢!”
“唉,我真羡慕你呀!我原本也是既干净又漂亮的,”一块满身是洞的橡皮,满脸愁容地说:“可是,落到我那淘气的小主人手里,你们看,扎得我浑身是铅笔眼儿,疼死我了!”“呀,这真太可气了!”橡皮们都替他打抱不平。橡皮们述说着自己在主人那里不同的经历,觉得各自的待遇真是天壤之别,有的高兴,有的难过。
正在这时,一块老年橡皮说:“我们要请铅笔帮忙,让它们给那些不爱护文具的同学写一张纸条,让他们醒悟!”橡皮们纷纷行动起来……下课铃声响了,同学们回到教室,一些孩子找不着橡皮,哭了起来。突然,他看见了桌子上的纸条:小主人,我那么愿意为您服务,请爱惜我吧!同学们后悔极了,他们决定找回橡皮,永远爱惜他们.从此,橡皮们变得干净极了。
生日聚会英语作文几句话【七】
有个朋友问我:“无产阶级的故事你会写么?”我想了一想,说:“不会。要么只有阿妈她们的\'事,我稍微知道一点。”后来从别处打听到,原来阿妈不能算无产阶级。幸而我并没有改变作风的计划,否则要大为失望了。
文人讨论今后的写作路径,在我看来是不能想象的自由——仿佛有充分的选择的余地似的。当然,文苑是广大的,游客买了票进去,在九曲桥上拍了照,再一窝蜂去参观动物园,说走就走,的确可羡慕。但是我认为文人该是园里的一棵树,天生在那里的,根深蒂固,越往上长,眼界越宽,看得更远,要往别处发展,也未尝不可以,风吹了种子,播送到远方,另生出一棵树,可是那到底是很艰难的事。
初学写文章,我自以为历史小说也会写,普洛文学,新感觉派,以至于较通俗的“家庭伦理”,社会武侠,言情艳情,海阔天空,要怎样就怎样。越到后来越觉得拘束。譬如说现在我得到了两篇小说的材料,不但有了故事与人物的轮廓,连对白都齐备,可是背景在内地,所以我暂时不能写。到那里去一趟也没有用,那样的匆匆一瞥等于新闻记者的访问。最初印象也许是最强烈的一种。可是,外国人观光燕子窝,印象纵然深,我们也不能从这角度去描写燕子窝顾客的心理吧?
走马看花固然无用,即使去住两三个月,放眼搜集地方色彩,也无用,因为生活空气的浸润感染,往往是在有意无意中的,不能先有个存心。文人只须老老实实生活着,然后,如果他是个文人,他自然会把他想到的一切写出来。他写所能够写的,无所谓应当。
为什么常常要感到改变写作方向的需要呢?因为作者的手法常犯雷同的毛病,因此嫌重复。以不同的手法处理同样的题材既然办不到,只能以同样的手法适用于不同的题材上——然而这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经验上不可避免的限制。有几个人能够像高尔基像石挥那样到处流浪,哪一行都混过?其实这一切的顾虑都是多余的吧?只要题材不太专门性,像恋爱结婚,生老病死,这一类颇为普遍的现象,都可以从无数各各不同的观点来写,一辈子也写不完。如果有一天说这样的题材已经没的可写了,那想必是作者本人没的可写了。即使找到了崭新的题材,照样的也能够写出滥调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