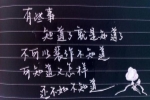清华大学作文450字【一】
清华大学是著名的高等学府,是我心中向往的知识圣殿,初中时父母带我去北京游玩,我们参观了清华校园,父母给我介绍清华的历史、名人与成就,我就立志将来要报考清华大学。
•我成绩优秀,综合素质全面,高中阶段每次重要成绩名列年级前列,高一期未获学校“万拓实验奖学金”一等奖,学业水平考试除化学操作技能获B等外,其余均为A等。我数学与物理学科特长突出,多次考试名列年级第一,高一获“希望杯”数学竞赛初赛二等奖、复赛三等奖,高二获“希望杯”初赛一等奖。
清华大学作文450字【二】
因为它的离心率永远是零。
我对你的思念就是一个循环小数,
一遍一遍,执迷不悟。
我们就是抛物线,你是焦点,我是准线,
你想我有多深,我念你便有多真。
零向量可以有很多方向,却只有一个长度,
就像我,可以有很多朋友,
却只有一个你,值得我来守护。
生活,可以是甜的,也可以是苦的,
但却不能没有你,枯燥平平,
就像分母,可以是正的,也可以是负的,
却不能没有意义,取值为零。
有了你,我的世界才有无穷大,
因为任何实数,都无法表达,
我对你深深的love。
我对你的感情,就像以e为底的指数函数,
不论经过多少求导的风雨,
依然不改本色,真情永驻。
不论我们前面是怎样的随机变量,
不论未来有多大的方差,
相信波谷过了,波峰还会远吗?
你的生活就是我的定义域,
你的思想就是我的对应法则,
你的微笑肯定,就是我存在于此的充要条件。
如果你的心是x轴,那我就是个正弦函数,
围你转动,有收有放。
如果我的\'心是x轴,
那你就是开口向上、Δ为负的抛物线,
永远都在我的心上。
我每天带给你的惊喜和希望,
就像一个无穷集合里的每个元素,
虽然取之不尽,却又各不一样。
如果我们有一天身处地球的两侧,咫尺天涯,
那我一定顺着通过地心的大圆来到你的身边,哪怕是用爬。
如果有一天我们分居异面直线的两头,
那我一定穿越时空的阻隔,
划条公垂线向你冲来,一刻也不愿逗留。
但如果一天,我们不幸被上帝扔到数轴两端,
正负无穷,生死相断,
没有关系,只要求个倒数,我们就能心心相依,永远相伴。
爱人是多么的神秘,却又如此的美妙,
就像数学,可以这么通俗,却又那般深奥。
只有把握真题的规律,的纲要,
才能叩启象牙的神塔,迎接爱人的怀抱。
清华大学作文450字【三】
从公共汽车站下车之后,第一眼就看见了清华大学的正大门,上面刻着这所学校的名字,接着,我们上去台阶之后,就看见了清华大学的主楼,中间种着一片草丛,两旁又有两栋很高的楼,看整个样子,就有着一种非常雄伟的.感觉,听妈妈说:“清华主楼,建于五十年代,现在是电机系、自动化系、计算机系、计算中心、网络中心所在地。”妈妈还说:“爸爸年青的时候,就在清华大学主楼的自动化系学习过。”听妈妈这么一说,我心想:爸爸在这学习过,他一定非常自豪,我长大也要像爸爸一样在这里学习。
清华大学大礼堂坐落于校园西区的中心地带,庄严雄伟,一直被清华师生视为自己坚定朴实、不屈不挠性格的象征。正前方竖立着一块石碑,这个就是清华大学师生的校训,它要让学生们时时刻刻要严格要求自己,我看了之后,心里暗暗地竖起了大拇指。
水木清华是清华园内最引人入胜的一处景地,地处工字厅后门外,四时变换的林山,玲珑着一泓秀水,山林之间掩映着两座玲珑典雅的古亭,正额“水木清华”四字,两侧“槛外山光历春夏秋冬万千变幻都非凡境”,“窗中云影任东南西北去来澹荡洵是仙境”,望着眼前的一切,我深深地陶醉了,心想:我小的时候一定要努力,长大才能努力成为一名清华学子。
清华大学呀!你真是一所名副其实的好学校,我将时时刻刻把你追求和向往。
清华大学作文450字【四】
清华,你好!
和你的故事要从头说起,虽然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开头可言。2008年,我参加自主招生考试,被清华降分录取。夏天自己拎着大包小包来学校,报道的地点已经有媒体围追堵截,要求我畅想校园生活,我那时说“记录生活的日子结束,生活开始了。”——奋不顾身飞蛾扑火,有“时间开始了”的自我感动劲儿。
如今我已大三,却还没有真正融入校园生活。现在在学校还常常迷路,同学讨论的成绩与保研,我也一头雾水。嘟嘟囔囔对学校的不满却说了很多,拿人不手软,吃人不嘴短。时值百年校庆,我想说给学校的,也不是感恩与颂圣,只能硬着头皮继续怨言。
因为身在学校,所以不能仅抱怨些片儿汤的话。白衣飘飘的年代没了,就别再紧紧拽住时间的裙角嗫嚅***;学术之不知礼之不存,也已经没有再捶胸顿足的必要;大师离去,微斯人吾谁与归。大势如此,学院当然不能幸免,所以也别再长歌当哭了罢。
然而,除去以上这些,我对大学仍有抱怨,仍有不满,仍有震恐,仍有大惊小怪,仍有不情之请。
大一、大二的时候,我喜欢拽着人聊时事。我的同学们总是左顾右盼坐立难安,一副盼着人把他们解救走的样子,实在被逼急才敷衍笑道:“社会就是这样的。”我那时还觉得奇怪,二十出头正是对社会敏感的时期,即使是纯生理上也应有些喷张和兴奋,可他们是如此漠然或畏葸。
现在我发现,他们并不是漠然,我的同学们不是不关心,清华人是可爱的,愤青少,领导多,内心大概还是有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悲壮,表现出来却是高屋建瓴,虚头八脑的……模样。
陈冠中的小说《盛世》里有个叫做韦国的青年人,他说:“我今年已二十四岁。二十岁那年我做的十年计划,正一步步实现,但我不能自满。***三十岁的时候在做什么?中共中央局五个委员之一。这样一想,我知道我要加倍努力了。”
我身边就有韦国这样的年轻人,这也不难理解,北大清华的学子一路都是教育和体制的少年既得利益者,成熟了,自然也是要沿着同一轨迹,而不能跌落到食物链的底端。于是,大学成了掠夺资本的地方。
我曾经旁观过学校的干部们做事,与教育和世俗标准下少年得志的成功者打过交道,他们青出于蓝地运用官场技巧与规则,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天真与成熟、愚昧与清醒、单纯与复杂、糊涂与揣着明白装糊涂,我无法分辨他们是哪一种,也无法分辨哪种更可怕。
百年校庆快到了,逢此盛世,锦上添花的话也不缺我一个人来说,泼冷水却是我所擅长的。往小了说,“母校就是你每天骂八百遍,但不许别人骂一句的地方。”往大了说,“为何我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那么,就此搁笔,是动情是矫情,就听收信人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