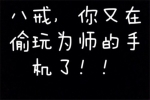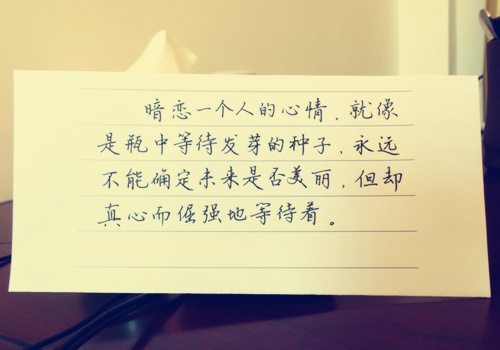
水与人作文600字【一】
有时,我会想,也许我是一个拥有着双重性格的人。
平静如止水
静的时候,也许会就着黄昏时阴暗的光线,看一份早已卷曲泛黄的报纸,嘴角擎起丝丝微笑,直至最后的阳光被黑夜吞噬。
静的时候,也许会深陷入那老旧的藤椅中,看漫天翻飞的黄叶落下,于是思绪,便被牵扯得绵长而悠远。
静的时候,也许会在某一个闲适而慵懒的下午,沏一盏清茶独坐窗前,静静的看细碎的光影舞于笔尖
再长长的呼出一口舒缓的气息;看那湛蓝的天空,眸中也渐渐洋溢那宁静的颜色。
有时,我会平静如止水,似乎与那承载着水的土地融为一体,也许心有波澜而面不惊,是的\',就是这样的静逸与闲适。
热烈如炙火
闹的时候,也许会笑上脸庞,笑得癫狂,笑得嚣张,笑得放荡,如酷夏那烈日朝阳直射下来,在人的皮肤上留下的那热情的痕迹。
闹的时候,也许会为某一件事而废寝忘食,做出一系列匪夷所思的事情,也许会有人嘲笑,然而已沉浸在了另一个世界的我,完全置之不理,一切心思都已火热的聚拢在自身。
闹得时候,也许会做出一些疯狂的事情,让人惊奇,让人无奈,让人不可思议,让人怒气冲冲,如迅猛的旋风席卷一切,吹得树梢摇晃,枝叶嘎啦作响,没错,就是如此狂妄,如此痴癫。
有时我会热烈如炙火,似乎整个世界都被我渲染,热闹一片,心中似海浪滚滚,翻出无限汹涌波涛,是的,就是这样的热情而奔放。
有时,我会想,若非水火相容,凝聚成灵,怎能化出一个我来?这一个水火共生的生命体?
水与人作文600字【二】
他们说,苏格拉底死于希腊民主。
这是一个不断自我膨胀的体系,在巴尔干半岛愈演愈烈,最后把一切与之相抵触的都推下了爱琴海。他们在民主的天空下,背倚着奥林匹斯山,喊叫着,横冲直撞,依稀还能听见公民,法庭,城邦,这些字眼。虽然只是口头的说说而已…既然公民就是一切,民主至高无上,那么,苏格拉底就不算什么,一个胡言乱语的疯子罢了,消失就消失好了,有什么呢?这是雅典的悲哀,民主的奇怪逻辑让人们失去了理智。
有时候想,控制确实不是一件好事,束缚住了手脚,久而久之,一切都僵化了,失去了生机,麻木了身躯,可不控制也不见得是件好事,当洪水来袭,没有堤坝,就会把一切美好都淹没在滔滔泥水中。在中国,死于专制暴政的名士固然不少,但正因为专制一统的存在,维护了一朝一代几百年的和平繁荣,不至于让万千大众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饱受战乱流离之苦。民主与专制就像水与岸的关系一样,只能疏导,不可阻挡。于是,便有了妥协。
我想,妥协,应该是人类文明没有被漫漫历史长河吞没的重要原因吧。在各式各样的文件上签下一个人,一座城,一方邦国的署名,然后用数十近百年的时间去遵守维护自己许下的诺言。用数十近百年的时间去思考发展自己脚下的土地。因为深爱身后的\'地方,所以双方各坐在了谈判桌的两端,心平气和的说着些美好明天,面红耳赤的争着些细小差别,然后在文件上郑重签下名字,满意而归。或许有些时候,心有不甘,但同时我们都知道,这已是最后的结局。如同1787年宪法,如同英国权利法案,如同尼布楚条约等等,战争打过了,流了许多血,死了很多亲人,百姓没吃没喝没住所,当初的怒气已变成了对灾难的悲痛,我们该坐下来好好相互理解,妥协了。妥协的背后,是人类的理性精神。不去恶意围堵,没有自我膨胀,引导水流向更好的远方,而不是强行阻之截之,如同大禹一般,治水应疏导。
水与岸,民主与专制,其实没有什么是绝对对立的,我们应该在对立中寻找统一,学着妥协,学着疏导。
水与人作文600字【三】
很久很久以前,水与土是一对冤家,他们常常一起比谁的本领大,可是每一次都分不出高下。
有一天,水与土还是和以前一样,在一起比谁的本领大。水说:以前都是自己给自己打分,这次不如问问别人,听听人家的意见,怎么样?土很不服气,因为水竟然可以想出一个这么妙的方法,而他自己却想不到。土虽然很不服气,但还是答应了。
随后,他们就来到了小河边,问一群小鱼:小鱼呀小鱼,我们俩谁的本领大呀?小鱼就说:当然是水叔叔哇!如果没有水叔叔,我们怎样生活下去你?水得意扬扬地说:哈!现在总算分出高下了。土不屑地看了水一眼,就急忙去找下一个目标。
接着,他们看到了小蚂蚁,就上前问小蚂蚁:小蚂蚁呀小蚂蚁,我们俩谁的本领大呀?小蚂蚁就说:当然是土叔叔哇!没有土叔叔,我就没有家;如果没有家我该到那里睡觉呢?土兴高采烈地说:哈,总算也让我赢你一个回和。水气急败坏地说:我就不信赢不了你。
后来,他们问了许多植物和动物,不是说土好就是说水好,问完一个又一个,水和土还是分不出胜负。最后他们都累坏了。突然,他们都想到了森林里最聪明的动物小仓鼠包包。
他们来到了包包的家,问:包包,我们俩谁的本领大呀?包包回答说:其实你们俩的本领一样大。水叔叔你可以让植物发芽,但如果没有土叔叔帮忙,植物也不会发芽。就因为你们俩常常比本领,不肯合作,现在弄得很多植物无法生长很多动植物都快死了。
水与火听后,感到非常惭愧,他们下定绝心,一起合作,分工。从此以后,他们成了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