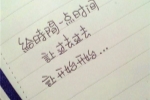高考景物散文作文【一】
黑夜下的街道显得更冷清了许多。
我如此喜欢着这个远离城市,只有平砖碎瓦的小地方。
就像一种隐居。
就像,某种疏离。
下班之后,挤过人肉饼后的公交,穿过城市繁华明明灭灭的光影。沉默中淡然且淡漠地以一种上帝的姿态注视着这短短旅途中形形色色的人群。
这让我想起小时候一个人穿越村外那个荒芜的坟场。多像啊,一样让人感到烦闷,一样让人感觉到窒息的绝望。
有许多骷髅在眼前摇晃,他们在笑,他们在闹,他们在低声交谈,偶尔向我投来一两瞥混不经意的目光。似十月凌晨里起床第一卷寒风。他们说着我听得懂听不懂的语言,在他们的大世界里游离张狂。
下车,深吸一口郊区里流畅到带清香的空气。便不再想走。
哦,忘了说,我住远离人群的风景区中,“十里河滩,湿地公园”。早上有金灿灿的阳光从尖头山侧升起,有蕴育朦胧轻纱似的薄雾笼罩的河床,以及那些水鸟、白鹭、话梅还有百灵。我总能在等公交的间歇间从那里寻到我梦的痕迹。
盯着久了,也就好似自己走在这样一场梦里,身前身后都是薄薄的一层我怎么看也看不透的雾,眼神无法聚集在远方,只能微微向前张开手,向前慢慢走,摸索着穿过林,穿过一个个串联起来的故事。
做完梦,亦或者梦还未完,公交车就像个姑娘似的来了。公交车本来是好的,记得初中时看过一句话:“希望总在未班车中开来”喜欢了很多年。可是现在,事实告诉我,我所喜欢的,往往将我载入我所讨厌的厌恶的,极度排斥的环境中去。 而我,却无力去反抗。
命运总是在妥协中四平八稳向前行着。每一个生命,或者类似于我这样的生命,都像是一个个早已在工厂流水线上排好了队向前行的产品。
尔后等待命运的大手将你归划到次品,还是合格品的行列。
那些顺从者的合格品,便端着红酒杯,出入酒绿灯红的世界;而次品,则在街角与秋风,与尘埃,进行一场思想上的交流。
但,人们只需合格品,因为他们站着高,享受欲理上的快感。
次品,在精神的田野上开垦,就算硕果累累,也终只在树的尸身上闪光。
其实,晚上的那条河那坐山,那些精致到让我沉醉的风景,我是看不到的。
也许,正是这样一种不可见,让我能常常走进它的梦里,走近它。听它的心跳,到它的温柔。
正是这样一种不可见的可见,让人充满向往,在绝望里为生命的生,所挂住的最后一丝留恋。
爬上五楼,打开房间前窗的纱窗,推开后窗的门,甩开鞋子打着赤脚然后泡上一杯热茶,或仰身倒于床上闭眼睡觉或举起一本在前晚还未看完的书或者拿出本,继续昨夜凌晨里的纠结。
多数时候,我是直接闭眼睡觉的,累或者其他。我不知道,要我说,也说不出来。
然后,到晚十来点的时候,起床,下楼,一遍一遍穿堂而过这片小建筑群里的街巷。穿越每一盏灯,抚摸每一块石,转角跑到一个陌生的角落,然后落寞地笑,间或抽上一根烟。
烟,慵懒地在夜里慢慢向上升,慢慢变淡融入黑的色里,好比一场朝圣,一段灵魂在解脱里向着天堂而去。
好像,一段故事。终被时间的庞大暗黑给吞噬。
“想起一个离开的人,就像拿起一把无形的刀”,某次,我对朋友说。他告诉我,所有的揪心,只是因为有一只手在紧紧握住回忆,握住一段枯萎了,再也复回不了的情。 我就笑,然后告诉他们滚。然后,他们就真的渐渐全部不见了。
这样也好,就没人再来打扰我,就没人再来说些不中听的话,做些连他们自己都明白的无任何意义的事了。
我也乐得清静,不是都说岁月静好岁月静好吗?这样真的挺不错的。
至少,我乐得做自己,不必管对错。
至少,我知道,在那遥远遥远的地方,存在着这样一个地方。
让死而复生,让时光回溯。
高考景物散文作文【二】
院子里静静地立着一株桃树。
农历三月的春风又一次吹起时,沉寂了一个严冬的桃树不经意地泛出了绿色,起初是枝条上浅浅的一抹,然后是一抹抹、一圈圈,渐渐由一根根枝条漾向树干,慢慢地整株桃树被染成了一片绿色。
要不了几天,春风的抚摩让枝条变得柔软起来,细细看上去,会发现鼓起了点点略带浅绿的绒包。第二天,竟冒出了细小的嫩叶,如丽人眉黛上的一点,娇柔地展在那里。似乎又过了短短一夜,推开窗户一看,竟是满眼的绿色,那桃叶已悉数舒展,嫩嫩地弥漫着。一阵细雨过后,闪着醉人的光泽。
心儿仿佛还沉浸在绿里,绿叶间却已在默默酝酿着花事。哪有多长时间啊?一个个小宝宝在春风里悄悄孵化,渐次睁开朦胧的睡眼,慵懒地卧在枝头,心底里却早就憋足了劲,只须三两缕和煦的微风,就一朵朵、一簇簇张开了粉红的笑脸。
不料夜间一阵短促的春雷,紧跟着是劈劈啪啪地响,全不是润物细无声的那般温柔。我心里在嘀咕,这场春雨过后,还真不知花落有多少。第二天早早起来一看,地上零零落落散着粉红的花片,待眼睛向树上看时,我却新奇地发现,那花并没有全部凋零,余下的残缺不全的花朵,还三三两两地傲立枝头。我的心为之一颤,忽然间明白了八百多年前陆游的感慨:“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这眼前的一切不正是这诗最好的诠释吗?是啊,风雨过后,满树桃花不再,但尚存的点点残红依旧回馈着这个缤纷的世界,依旧傲立枝头,依旧在风雨中继续演绎着自己不败的花事。不管经历过多少的风霜雪雨,明年的三月,满树的桃花依旧会怒放枝头……
高考景物散文作文【三】
例如,朱自清先生《春》“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小草偷偷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儿……”作者写的是春山、春草、春花,本来是静态中的物,而在文章中却呈现出动态,这也是化静为动的写法。作者把静物写活,一是用了拟人的手法,一是用了表示动作的词语,如“钻”、“让”、“赶”这些词语赋予某些人的动作。
高考景物散文作文【四】
国庆前夕,朋友说自驾到庐山走走,只是随意地一说,哪知欣然成行了。
我们是国庆前一天下午到九江的。第二天天刚亮,从九江宾馆出发,不久,就开始登山了。说是登山,其实是车载我们上去的。二十余公里绕来绕去的盘山公路,我们小心地走了四十余分钟,才来到庐山山门口,真是“跃上葱茏四百旋”。一看手机,整七点。站在门口,伸了个懒腰,正欲踏步入门,忽听说离牯岭镇尚远,牯岭镇才是景区的起点,我们忙又驱车向前。
“牯岭镇”是庐山行政管理机构所在地,海拔1116米。月牙弧形的山镇随山脊而建,石墙红瓦,屋舍俨然;街心公园里一头斜卧的石牛雕塑,鲜活欲动,著名书法家启功题写的“牯岭”,镌刻在基座上;近旁曲径小道,憩亭昂然,茂林娇花,芳草萋萋,俨然一座美丽、别致的高山小城。街上到处停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小车辆,林立的商家店铺里满是进进出出的人,而且车还在不断地进,人还在不断地涌。车来人往,熙熙攘攘,我们仿佛置身于天街云市中。
我惊讶于近两万人在这样远离尘嚣的高山岭镇,过着自在而舒心的日子,他们各安其所,各做各的一份儿事情,又把自己的家园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难怪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在游庐山康王谷后要写《桃花源记》呢,敢情的确有这样的好地方,莫非这里就是桃花源?
我正纳闷,同行人说赶快找个饭店,先填饱肚子再说。走了几家早餐店,也都是客满,只好认定一家,站在门口等了好一会,前客让后客,才挤上了座位。匆匆地吃过早饭,请了导游,我们走进了牯岭东边的西洋别墅区。
初阳东升,曲折而来又蜿蜒而去的长冲河畔,一幢幢造型别致,风格不同的西洋别墅,躲在密密的林荫里,安详而静谧。这些西洋建筑风格的别墅,据说在庐山有近千幢,都是当年西方传教士来庐山传教留下的,而这里最为集中。无怪乎,胡适说牯岭是“代表西方文化侵入中国的趋势”。
面临长冲河,背依大月山的“美庐”别墅,石墙木构,两层建筑,明快简洁,充分体现了“庐山房子铁皮盖”的特点。这幢别墅是1934年,英国的巴莉女士赠送给宋美龄的礼物,后来一直是蒋介石夫妇的夏季避暑官邸。1948年8月,蒋介石因喜爱这里而特别命名为“美庐”。“美庐”既贴切了优美的环境,也暗合了蒋夫人的名字。也正因为“主席行辕”的缘故,当年在这里曾出炉过许多令世人瞩目的事件。庐山军官训练团的创办,国民党围剿中央红军计划的炮制,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谈判,对日全面抗战的酝酿和决断,美国特使马歇尔八上庐山的“调处”等等,这些都给小楼披上了扑朔迷离而又极为诱人的面纱。我们徜徉在这里,看着基本还原的物品陈设,想到了他们曾经有过的生活温馨与光灿,也想到了在这里演绎的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政治风云。
从历史的遐想中方醒,我们已漫步出美庐,过芦林湖,就已完全被围在茫茫的林海里,天空只能透过高高的林梢,渺茫地看到一点点。这些树木,仿佛墨线拉过一样,借着阳光、雨露,都拼命地伸长脖子往上长,而且一律向上。地上满是陆离的树影,斑驳可人,身旁潺潺的山溪,一路欢歌。
过了幽幽的林荫,我们到了石门涧景区。站在石门涧堤坝上,一边是深碧的水库,一边是绝壑幽长的深崖,四围都是满目的奇峰秀峦。我们乘缆车,很快又来到了凌空斜拉悬索桥上,这里是一个很好的观景台,上可以赏重山,下可以览奇石。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说:“庐山之北,有石门水,水出岭端,有双石高竦,其状若门,因有石门之目焉。水导双石之中,悬流飞瀑,望之连天,若曳飞练于霄中矣”。“双石”我是找到了,天池山和铁船峰,对峙如门。左边的铁船峰,孤峰兀立,峰脊高平,从南往北如马背,而在谷口处陡然直下,犹如刀砍斧斫,壁立千仞。“芙蓉削出插天半,千尺无枝不着土”。鸟不可飞,人不得攀。右边比肩的天池山,高大巍峨,树高千尺,相比之下虽缺少了些挺拔的雄姿,但双峰对垒,谷深难测,仍不失震慑魂魄的气势。两峰从中间敞开一条通道,折向西北,宛如天门中开,佛光乍现,给人开阔明亮的畅快。自然造化的鬼斧神工,委实令人瞠目结舌!“望之连天,若曳飞练于霄中”的瀑水,却成了断断续续如线的细流,露出了涧底数不清的断石残岩,在秋阳下,有些晃你的眼,峡谷却更加的幽深了。
晌午时分,我们来到了石门涧的上游,乌龙潭和黄龙潭。相传很久以前,黄龙山谷中有两条桀骜不驯的黄龙和乌龙,时常争斗,引发山洪,周围百姓无法安居乐业。后来彻空禅师云游到此,听说这件事后,运用法力将二龙分别镇在黄龙潭、乌龙潭中。两潭一南一北,很近,如果与石门涧相比的话,这潭就有些小家碧玉了,但瀑水却远远地超过了石门涧。乌龙潭的泉水在斑驳的树影里,大大方方地从罅岩中挤出,淌过光滑洁净,各呈姿态的岩石,敞亮地流入石门涧水库。黄龙潭就有些害羞含蓄了,躲在凹谷里,自一方绝壁上,银练般飞天而降,集于暗绿深潭,弹出皓白的水花,发出沉闷的轰鸣声。湿漉漉墨绿的苔痕上,还有几处石刻。据说它却是个好运潭,很讲究的清泉洗手,会给你带来好运,什么一遍洗手怎样,二遍洗手如何,洗四次最好,可惜我已记不清楚了。但确有很多好奇的游客,在凸起的乱石间掬水洗手,祈求好运,有的不顾泉溅身上,误入他人的镜头。出门在外,祈求好运的心理肯定是有的,尤其是平安运。
回到石门涧,我们在这里简单午饭后,就赶往含鄱口,哪知路上的车辆实在是太多了,任凭交警手忙脚乱,收效却是很小的。约下午四时左右才到。
含鄱口,满野的竹林松海,蓊蓊郁郁。一方石构牌坊上的“含鄱口”和左右的“湖光”、“山色”刻字,在西照的夕阳里,金光闪烁。听说站在含鄱亭,是观日出的最佳地之一,可惜已是傍晚,远天把薄薄的暗纱,悄悄地洒在我们的周围。人很多,为了不耽误返程的时间,我们坐缆车往星子县大口瀑布。
大口瀑布又叫彩虹瀑布,雨过天晴以后,可以从灿烂的阳光下看到五颜六色的彩虹而得名,是真是假,我是无法看到了,几天没有下雨。缆车很快把我们载到了一座山岭上,远处鄱阳湖的浩渺烟波与天相接,朦朦胧胧,分不清哪里是天,哪里是湖。周围层岩穿空,万象顿生。并列的山脊仿佛一排排的战马,整装待发,折叠的山石星星点点地攀沿向上。仙人指路石,似乎端坐在欲飞的雄鹰背上,昂然翘首在天外。身旁是奇形怪状的山石,裸露着,峭楞楞的。石缝里一条曲曲弯弯的尺许羊肠游道顺着山脊,不断地忽左忽右,进进出出的游人在石缝里穿来穿去,仿佛行走在半空中。聪明的摊贩们没有忘记生财的机会,他们在山脊崖壁上凿石钻孔,硬生生地铺排一溜平台小屋,栈道般悬于半空,既能给这里增添一道令人兴奋刺激的风景,又能让游人享受惊险的同时轻松购物,真可谓两全其美。
我们好不容易闪闪避避小心翼翼地下到半谷,站到了神浴潭旁。只见一绺细水从两山夹峙间凌空而落,在高可百米处,好像遇到挡道的山岩,瞬间分为两股,不断地撞击沿途累石,散成无数碎银,而在临近瀑潭时,又汇成一股跌跌撞撞地迸落于神浴潭,然后在潭里打了个滚,又匆匆而别,直入万丈谷底。
几次想站到留有李白《望庐山瀑布》诗石刻旁,人、诗、瀑合一,想象一下当年李白“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壮观气势,但无奈被专门在那里拍照揽生意的摊贩叫了下来,说是要收费。不照就不照呗,反正水也不大,倘若遇雨,那自高空临崖飞流的景象,那声震空谷响彻天宇的气势,洋洋大观,我肯定是要站上去的。
神浴潭不大,约百十平米,上方大岩上刻有“彩虹”、“仙搓”,这是绝美的佳处。各路神仙驾着彩虹、鸾车纷纷来这里休闲洗澡、搓背,惬意地享受一把人间的美景。真是人间落仙境,世外有桃源。
回到含鄱口,已是晚上六点四十分,四周静寂,此起彼伏的松涛伴我们一路来到停车场。
到牯岭,已是万家灯火。
高考景物散文作文【五】
“动静结合”指的是动态描写和静态描写有机结合起来描写景物。仅有动态而无静态描写,会使文章显得单调;仅有静态而无动态描写,则会使文章显得死板。只有把动态描写和静态描写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呈现事物丰富多彩,气象万千的情状,才能使文章有曲折起伏、摇曳多姿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