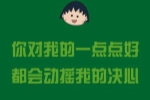不变作文【一】
披着月光漫步,偶尔仰头看看那昏暗的路灯,身后的影子被留恋的灯光拉长,和四周的景物述说着对家的思念。天空中那弯弯的月牙又勾起了谁对家的记忆,望着这月亮,想到家人正和我一起沐浴着这月光心中便充实了许多。
不记的刚读寄校时的害怕,却铭记了家中的温馨;
不记的在学校的第一个夜晚是怎样入睡,却想起了家中那张温暖的大床;
不记得食堂的饭菜是如和的难咽,却回味起了家中常吃的佳肴。
永远记得第一次读寄回家校回家时的情景。那时才七岁,到家中时父母向我寻问些学校的事。记得当时本来还保持着一点小男子汉的气慨,硬是撇着小嘴不哭。到后来父母提问的语气越来越激动,他们目不转睛的看着我,一脸认真,有时听我讲到某些事的时候脸上写满了欣慰。他们侧着头竖起耳朵,爸总是横眉紧锁,妈则是带着淡淡的笑意,像是在听一个极有趣的一个故事,专注的神情好像不想漏下一个字。以至于后来我讲到伤心处就一下子扑到他们怀里大哭起来。这是爸脸上才浮起点点笑意,嘴角勾起一道弧线,双眼微闭,用手轻拍我的头。妈则是一脸凝重,轻声说一些鼓励我的话还和爸说了一些我那是听不太懂的话。我一直认为家永远可以让我依靠。
是间总是偷偷的流走,一眨眼,时间过去了八年。八年里,我不段在变化从以前的爱哭的.小屁孩到现在的高一小子。我慢慢学会了独自承受外面的一些风雨,而他们常说的话也从“你还小”变成了现在的“我老了”。唯一不变的是我始终认为家永远可以让我依靠。
就在上一次放假回家时,快吃午饭时。父亲比量着我的身高,一手搭着我的肩膀一手轻轻的按着我的头,还是像以前一样满脸的笑。只是眼神中多了些满足眼角挤进了些皱纹。父亲边比量着我边说:“好小子都比我高了”父亲的语气中有些得意。“恩”我兴奋的应了声。随后目光落在了父亲身上,父亲一米七五的身高,身体以不复当年强壮有些偏瘦,微黑的脸在两边几根白发和中间那浅黄的眼珠的映衬下现的有点沧桑。“爸”我轻轻的叫了声。“怎么了?呵呵”父亲的脸上依旧堆满了笑。“没什么”我心里有点不是滋味,尽量避开父亲的目光。“呵呵,这孩子”父亲又说道。“我去帮妈盛饭”我找了个理由回避父亲。来到厨房看到母亲在拿碗,我便过去接。“不用,你难得回家一次,等下多吃点。”母亲微笑着说。而我的目光却落在了母亲那双爬上皱纹的手上。我的视线模糊了,心中牢牢的记住了9月30日和10月5日这两个日子——这是他们的生日。家在给我依靠的时候也在变化着,但唯一不变的是我始终认为家永远可以让我依靠。
回过神来自己已站在月光下许久,家中的人一定也和我一样沐浴在这暖暖的月光下吧,口中喃喃道“明天就可以回家了。”脸上浮现出淡淡的笑意。家,始终是我永远的依靠。
不变作文【二】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春风桃李,落叶梧桐。万物灵长无时无刻不在改变着自己音容相貌。好像自然的事物没有是什么亘古不变的。但是不变与变化应该是互相依附的存在。
执子黑白的人生,落在经纬交错的方格中,步步为营,如履薄冰。他以宏观万变,应对棋局的沧桑巨变。吴清源先生的人生就是这样,他与他的棋子落在那个格局混乱的民国时代。棋局上的他,以诡异简洁的手法,变幻莫测的棋局,让对手“繁华殆尽”棋局之外的他,同样是一个随世事漂泊的,一个只心系围棋的独行者。而无论是在对弈中还是生活中,吴清源先生都是以万变之化,应对万变之事。
“百读红楼百动心,哪知春夜尚寒侵。每从细笔惊新语,重向高山愧旧琴”这,就是文学泰斗周汝昌先生一生的精神写照。
当初曹雪芹耗尽毕生心血,历经十年沧桑,在“红楼”的笔耕中走到了他自己生命的尽头。而文学大师周汝昌,在研究“红学”长达六十年的旅途上,同样奔走到了他生命的尽头。可谁知,在这条生命的长跑中,他所度过的心酸苦楚。年少的周先生,治学书画,丝竹粉墨,无一不精。他虽生于书香门第,但是他的年少时光却是在那个哀鸿遍野的社会里听着军阀混战的炮声度过的。而引领他走上红学之路的是与胡适先生的一次偶然相遇。从此,这位红学大师真正的旅途便开始了。无论是长达八年抗战,还是对文学家地狱般的文革,都没有丝毫击退这位大师前进的步伐,当周先生完成他当初对胡适先生的提议时,已经度过五十六个春秋,于是百感交集的'周先生赋诗道:“五十六年一愿偿,为芹辛苦亦荣光”他用他那一生未变的宏愿,勇敢的应对中国百年的沧桑巨变,当真是“以不变应万变”
无论是万变的吴先生还是不变的周先生都已经远离了我们,而在生活中迂腐的人永不改变,趋炎附势的人变得过火。大抵都是因为他们对生活与未来充满迷茫与恐惧,以至于迷失了自己,而历史在永恒的变化中,终将会模糊这些人的印记。不被世人所追忆。
吴清源先生和周汝昌先生的身上都存在着“不变”与“变化”至于原因,在我看来,两位先生甚至是许多伟人,都有着一个永恒不变的信念,来抗击世事的沧桑巨变。
所以不变的信念就好像未经雕刻的胚玉,在历史的如刀般的变化中,坚持本心,终将会刻出令人敬仰的雕塑。